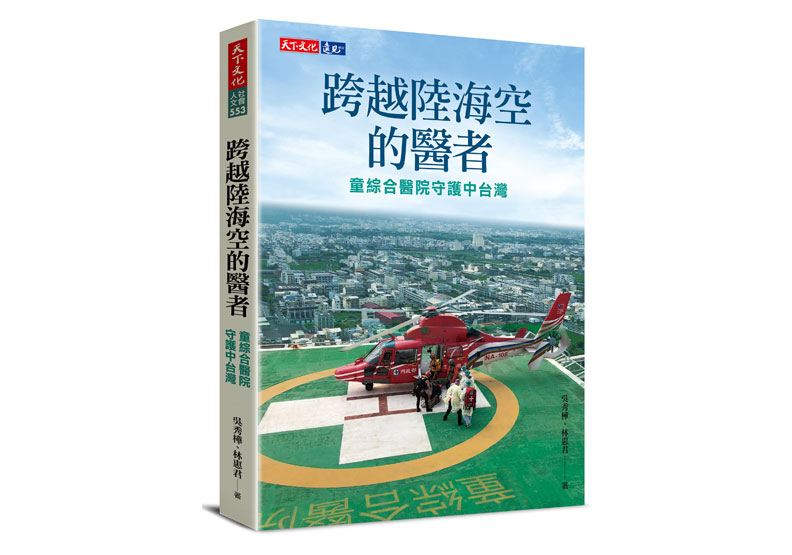清晨天才濛濛亮,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簡稱空勤總隊)的海豚直升機已經載著兩位童綜合的護理師,從台中清泉崗機場出發前往烏坵,預定載運一位因心肌梗塞而急需醫療後送的民眾。
兩個多小時後,火紅機身的海豚直升機緩緩降落在童綜合頂樓停機坪,在此等候的急診醫學部人員立即將病人放到推床上,直接送入急診室,隨後快速抵達心導管室檢查,再馬不停蹄送進手術室,進行血管繞道的緊急手術。
由於充分掌握了心血管疾病的黃金救援時間,患者在幾天後平安出院,返回烏坵。
海事救援成為日常
在童綜合急診醫學部,每天所要處理的業務,用「海陸大餐」來形容也不為過,除了必須救治救護車送來的病人,平均每年還必須處理5件至15件直升機轉送案例。來自空中的案例,除了離島居民,還有不少海事工作人員,幾乎已經成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最近一個案例,就發生在2022年3月。
一艘蒙古籍貨輪行經台中外海,發生事故沉沒。接獲消息後,空勤總隊火速前往,將落海的七位船員救起,送往童綜合急救。
此時,空中救援任務結束,但童綜合的考驗才正要開始。
疫情期間,搶救生命固然重要,但醫護人員和院內病人與家屬的安全同樣重要。如何兩者兼顧?
「我們把船員安置在急診室外的獨立觀察室,以及負壓隔離艙中進行急救,」童綜合醫療副院長吳肇鑫說。
可是,為什麼海上事故,會把病人送到童綜合?
「因為我們總是預先做好準備,台中外海離岸風電施工人員、航行在中部外海的各種國際船隻,一旦有緊急醫療需求,空勤總隊載運病人的直升機總是優先選擇送往童綜合治療,」吳肇鑫補充。
他口中的「預先做好準備」,指的是,在醫療技術與設備之外,還必須要有周邊配套規劃。
規劃配套,把時間留給醫療
如果只有醫療技術能力,卻無法將病人及時送到醫院,或因為環境條件不足而影響救治時機,也是枉然。因此,童綜合在梧棲院區醫療大樓頂樓設有標準的空中救護直升機停機坪,協助直升機在最短時間內順利停降;此外,童綜合在直升機停機坪設有空中急救室、空中急診重症處置區,當病人抵達醫院停機坪時,急診醫生便可以立即進行治療,或者經急診專屬電梯直達急診室,把更多時間留給醫護人員。
然而,急重症患者可以透過直升機接送,但有些疾病不緊急,卻無法放任不理,又該如何是好?這種情況,在離島地區格外容易發生。
以烏坵為例,日常飲水、生活用品與交通,都只能依賴每15天一班的船運支援,更別說是其他;一般民眾如果有醫療需求,只能靠海軍設在島上的診療所,提供簡單的治療。
視訊遠距醫療,把握黃金時間
為了消弭醫療落差,童綜合從2022年開始,提供當地視訊遠距醫療;若有緊急後送需求,則會派遣護理師隨機,提供完整照護。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為了做好離島與海上船隻緊急醫療後送服務,急診醫學部的醫護同仁都必須學會如何從直升機接送病人,因此童綜合會安排他們定期前往空勤總隊接受訓練,」吳肇鑫說。
救人急如星火,但是並非直升機降落後,就可以立即推出病床接運病人。
吳肇鑫舉例,直升機降落後,旋翼仍在轉動,帶動強大的氣流,可能將周遭物品捲入,醫護人員要注意身上的衣服和吊牌、推床的床單,可能隨風飄起,卡在旋翼上,稍有不慎便容易受傷。
「從人員登上直升機到當地接運病人、患者上機時的照護、降落後人員的護送、等待的醫護人員何時可以推床接人、如何靠近直升機……,每個環節都要配合指令動作,都必須靠著定期訓練內化成習慣與標準作業流程,才能讓各個細節盡善盡美,」吳肇鑫強調。
做好第一線的「拆彈人」
海上急馳救援之外,童綜合急診醫學部在陸地上也搶救了無數生命。儘管只是區域級的私人醫院,但每月急診量高達6千人次以上,與鄰近的醫學中心不相上下。
吳肇鑫用「第一線的拆彈人員」,來形容童綜合急診醫學部的工作情況。
「我們在面對炸彈時,不能只是把導火線剪掉,就交給接手的人;第一線的人要把會引爆的裝置全部拆除,才能交接給下個階段的人員。就像遊戲闖關一樣,需要一關一關來,只是我們必須審慎對待,不能有差錯,因為生命無法重來。」
這段過程,團隊合作相當重要。急診部護理人員接到派遣救護車的電話時,不僅要詢問病況,還必須同時做出要調配哪些人、多少人來支援等判斷。
吳肇鑫分享:「曾有護理師接到要求派遣救護車的電話,內容是台中清水有位懷孕37週的婦女,突然意識不清、陷入昏迷,於是她馬上抓住關鍵字『孕婦』、『昏迷』,判斷可能是羊水栓塞導致。
「儘管羊水栓塞很罕見,但死亡率超過90%,而且救護車到達現場後,發現孕婦癲癇發作,並且從家屬口中得知,孕婦同時患有子癲症,讓整個情況變得更加危急……
「在救護車前往載送病人到回院這段期間,急診醫學部召集了婦產科、小兒科、麻醉科、心臟內科與外科,以及裝葉克膜的體外循環師(簡稱體循師),多個專科共同待命。
「孕婦到院時,牙關緊閉、全身抽搐、口鼻出血、皮膚冰冷,並且量不到血壓……,於是,急診醫師幫孕婦做CPR(心肺復甦)、插管,再施打急救藥物,先控制癲癇。
「此時,已來不及送患者到開刀房,婦產科醫師直接在急診室進行緊急剖腹產手術,嬰兒隨即由小兒科接手,同時進行CPR及送往新生兒加護病房治療;孕婦則交由心臟外科接力,裝設葉克膜並進行急救。
「一共輸了3萬多西西的血,相當於一個成年人身體血量的七倍。等到孕婦狀況稍微穩定,判斷她應是羊水栓塞合併瀰漫性血管性凝血,還好最後母子均安。」
然而,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同樣是羊水栓塞的案例,有超過九成的病人,即使僥倖救回來,卻陷入無法恢復的昏迷狀態,」吳肇鑫說明,「童綜合團隊充分合作,輪番利用高品質的CPR、剖腹產取出胎兒、建置葉克膜,是當時能夠快速、成功救回那位孕婦的最大關鍵。」
急診醫師沒有後悔的機會
「童綜合急診醫學部一個月平均要收治五位急產孕婦、裝設一次葉克膜,」吳肇鑫直言,「這樣順暢的團隊合作,不可能一次到位,過程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磨合與調整,各科放棄本位主義,彼此了解與學習,聚焦在『如何做對病人最好』的核心理念,逐漸凝聚共識,才得以完成一項又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也因為這樣,「急診醫學部可以說是與各科配合最多的部門,必須派醫師到各科學習,增加彼此的了解,才能建立更完整的標準作業程序,」他認為,「急診醫師的價值,就在於當下做出最正確的判斷與處理,沒有機會事後悔恨『當時我怎麼不這樣做』。」
「對急診醫師來說,到院後的前十分鐘是很珍貴的,而且只有一次機會,只要錯失就會對病人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因此急診醫師要做到『快、穩、準、狠』,即刻判斷『怎麼做』、『如何做』是對病人最好的,」一貫面帶微笑的童綜合急診醫學部主任魏智偉,談到這個話題,神情變得凝重。
時效不是唯一考量
急診重視時效,然而,有時候,最快速、最有效的治療,未必是最好的選擇。
魏智偉舉例指出,童綜合附近有很多工廠,一旦發生工安事故就會送到童綜合,最常見的就是手指或手掌不慎捲入機台,造成夾傷或斷裂,必須透過整型外科進行顯微重建手術,將被切斷的手指骨頭接合,再讓肌腱、神經、動脈、靜脈吻合,讓血液循環重新流動,最終才可望讓斷肢、斷指恢復原有功能。
「從手指被切斷到接回,必須在6到8小時內完成,而且必須全程妥適保存斷指,才有機會在手術後恢復功能,但在過程中,醫師還必須同時為患者傷口清創,並且考量怎麼做才能讓患者維持原有生活,」他說,「五隻手指中,急診醫師會優先保存大拇指,因為手部約有50%的功能會用到它,其次則是食指與中指,『維持器官最大功能』是收治病人時的第一優先考量。」
可是,有時因為工傷或交通意外,斷肢已經支離破碎,「截肢是最快的方式,但患者之後就一輩子都是身障人士,未來生活何以為繼?如何度過漫長、艱辛的重建之路?急診醫師都必須設身處地考量,」魏智偉語重心長地說。
甚至,有時不能只從功能面考量,還必須從心理面換位思考。魏智偉談到,他曾經遇過一位病人,因為操作不慎,整個手臂遭機台捲入。送到醫院時,明顯手臂功能已無法完全恢復如初,但病人堅持要保留自己的手臂,急診醫師便先清創,再交給骨科與整型外科,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重建手術。
「雖然過程漫長,治療時更是痛不欲生,最後留下來的手臂功能也不及原來的完整,但終究完成了病人希望留住自己手臂的願望,」魏智偉語說。
膽大心細,隨時做出正確判斷
相較於其他專科醫師只要專注自己的科別,魏智偉笑說:「急診醫師根本就是一個『斜槓』的專科,有時還得要上演全武行,很多想都沒有想到的情況,確實就是會發生。」

有時,患者的手指意外卡在鐵椅的洞裡,拔不出來,只能連人帶整張椅子一起去就醫;或是被蛇咬了,直接帶著被打死的蛇去打血
急診工作高度仰賴團隊合作,童綜合在2000年便組建了急重症照護團隊,強化緊急救護能力。
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急診醫師除了基本的內、外、婦、兒、急診、眼、耳鼻喉與精神科,連同緊急醫療救護、災難醫學、高壓氧治療等,全部都要會。
另外,急診的「常客」之一,是自殺或者家暴受害者,急診醫師必須能夠辨識,病人身上的傷口,是否真如患者或陪伴者所說,是「跌倒」、「摔傷」造成;尤其,有時陪伴者可能就是加害者,那時就必須將病人帶離陪伴者,再引導病人說出真相,同時檢視患者傷處,進行通報。
「膽大心細,隨時做正確的判斷,這就是急診醫師的特質,」魏智偉直言剖析。
小兒專科醫師守護兒科急診
隨著時代進步,急診醫學逐步演化,台灣從2010年起施行五級檢傷分類,做為判別患者治療先後順序的標準,依病情嚴重度決定看診次序,不再「先到先看診」,讓醫療資源運用可以更有效、適時,及時挽救重症者的生命。
不過,這個概念,童綜合落實得更早。
吳肇鑫說:「童綜合早在2000年就開始建置急重症照護流程,組建急重症照護團隊,強化緊急救護能力,目前我們第一線的急診醫學部急診主治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與住院醫師,合計超過一百位的人力配置,其中更包含三位小兒專科急診主治醫師。」
成人急診醫生不能看兒科嗎?
國內醫院在急診中設置小兒科專科醫師的情況本就少見,童綜合還編制四位專任、三位兼任,為什麼?
「不能把兒童當成『小大人』來醫,」魏智偉指出,「兒童不僅體型和成人有差異,生理變化和組織結構也和成人有許多不同。因此,儘管急診專科的訓練也包含小兒急症處置,但是為了更加提升海線兒童醫療品質,童綜合還另設三位小兒專科醫師堅守兒科急診,24小時守護兒童健康。」
培育雙專長急診醫師
在高壓的醫療現場,急診醫學部更是經常得面臨生死交關的場面。如何讓醫師在高壓工作下保有熱忱與專業,就得靠前輩的提攜與手把手的經驗傳承與教學。
魏智偉補充:「急診原本就是手把手的教學,童綜合為了培訓更多人才,除了招募其他醫院的急診醫師投入,更從住院醫師開始培訓,從2013年到2022年5月,共訓練了23位住院醫師取得急診醫學專科醫師證照。」這些醫師不僅有急診專長,童綜合還希望把他們培養成具有雙專長的醫師,如:急診加重症、急診加高壓氧等,以應付更多不同病況的急診患者。
「願意給機會、訓練接班,急診醫學部這種一脈相承的教學模式,讓童綜合這個『品牌』在醫學系學生間留下不錯的口碑,」魏智偉說。
近年來,急診室工作負荷量大,年輕住院醫師往往不願投入,但以召募急診住院醫師來說,在鄰近醫學中心無法滿招的情況下,「童綜合要招募兩位急診住院醫師,卻有十位來申請,」魏智偉表示,「顯示童綜合急診醫學部的醫療實力受到相當肯定,讓住院醫師想到這裡學習。」
不過,童綜合急診醫學部的口碑,不只一種。
魏智偉說:「急診不只是急診,我們還協助醫院發展高壓氧、傷口照護和支援各種大型活動,如:媽祖遶境、日月潭泳渡等,讓急診醫師的發展更多元。」
認識自己,明白你是病人的唯一
在醫療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終究有無力可回天的情況。
「有時病人明明救不回來了,但是家屬堅持要再救,這種心情當然能明白,但再救不僅是無效醫療,承受的更是已逝的病人肉體,於是該如何向家屬說明,就要講究技巧與方法,」魏智偉半開玩笑地說:「因為要在短時間內向病人說明情況,並且讓家屬可以體諒,我的口才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他曾經收治一位急診病人,經過搶救,最後仍撒手人寰,但是當他走出急診室外,向家屬說明時,家屬並未直接奔向過世的親屬,而是帶著女兒向他鞠躬道謝,因為家屬知道醫生已經盡力了。
這是一種面對生命的態度,你必須認識自己存在的意義。
「一位醫師一天可能得面對好幾位病人,但是在病人眼中,醫師卻是他們的唯一;急診醫師的責任更重,因為在危急的情況下,我們是唯一可以向病人或家屬說明的人,讓他們能夠信任我們、放心交給我們,」魏智偉強調。
童綜合在急診醫學領域已打下相當的口碑,但展望未來,「急重症治療是童綜合的專長,之後除了持續強化急診與重症實力,也要再精進罕見疾病的治療與處理能力,讓台灣的醫療與世界有更多交集,」吳肇鑫說,「要做到這些,必須讓教學與研究更深化,培育更多住院醫師,才能造福更多病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作者為二十餘年財經科技記者 吳秀樺、多年醫藥與財經記者資深媒體人 林惠君。原文節錄自《跨越陸海空的醫者:童綜合醫院守護中台灣》/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