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對孝的定義太狹隘,孝不是個形式,回到精神科的本質「心」才最重要,不管將家人送到哪裡,重要的是愛的延續。我時常遇到家屬在診間哭,掙扎是否要送罹患失智症的家人到機構接受照護,家屬陷入孝順糾結,擔心失智症家人感到被拋棄,難以決定。
孝道的定義、失智照護的觀念,都該與時俱進
隨著失智症照護品質提升,及早就醫確診的個案增多,平均壽命延長,照護超過10年的失智者不在少數,失智症
照護的旅程變得更加漫長。
當失智症的照護上升到比較專業的等級,有些家庭會開始考慮將失智者送至住宿型照護機構,家屬不知如何跟失智症親人開口,在難以逃避的現實中,被價值觀的形式困住,內心十分痛苦。
到了機構的爺爺病情穩定,奶奶也逐漸放下當初的糾結,卻因為生活突然失去重心,脫離了照顧者的主要角色而
適應不良,經歷憂鬱、焦慮與失眠,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才逐漸好轉。
很多家屬會在診間問醫師,是因為做不了決定,或是想詢問專業意見,或希望由醫師說服失智者。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資源和狀況,機構也並非是唯一的選擇或最好的答案。醫師會替家庭分析所能利用的資源和制度,說明優、劣勢和未來可能遇到的挑戰,其中也牽涉到人力與金錢,必須讓家庭照護者有概念做好準備。
會決定將失智者送往機構照護的家庭,通常是一開始還是在社區中照護,或是透過居家照顧滿長一段時間。照顧失智者的過程,照護者也學會如何變老,這個課題同時也挑戰他們自己對生命意義與價值、長短的看法。每個人所做的決定反映我們的價值觀,醫師作為助人的角色,會提醒照顧者這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決定,現實上做不到不代表沒有愛,從中調和降低家屬的愧疚感。
即使是失智者,也有靈性的需求
失智者也有知的權利,對輕度失智症的失智者據實以告,說明到機構照顧的利弊與困境;中重度的失智症雖已分辨不出空間地點,以善意出發、重點說明,不強調負面意義,可以說要去另一個地方住,白天會有很多人比較熱鬧、安全,失智者雖未必全聽懂,卻也是一種心意。
有時失智者早已不知自己身在哪裡,是家屬及照顧者過不了心裡的關卡,難以開口,可能陷入了道德倫理的框架中,而忽略自己對失智者的心意,這並不是拋棄,只是換了一條路讓失智者有機會可以被照顧得更好。
面臨後期階段的失智症,其終點不像癌症好預測,病情反覆的過程也會讓照顧者內心動搖、害怕,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平靜地面對死亡。許多家屬在陪伴失智症家人的最後一哩路上,希望能尋求安寧緩和醫療的協助,卻不知如何尋
找銜接相關的資源。
安寧緩和醫療追求善終,靈性的探討則能超越人的極限,綜觀台灣在照顧及失智者心理層面上的支持仍舊不足。即使是失智者,同樣也有靈性的需求,有權以平和圓滿的方式迎向終點,我們對處理死亡的觀念應該與時俱進。
❝有時家屬及照顧者陷入了道德倫理的框架中,而忽略自己對失智者的心意,這並不是拋棄,只是換了一條路讓失智者有機會可以被照顧得更好。❞
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老年精神科主任 蔡佳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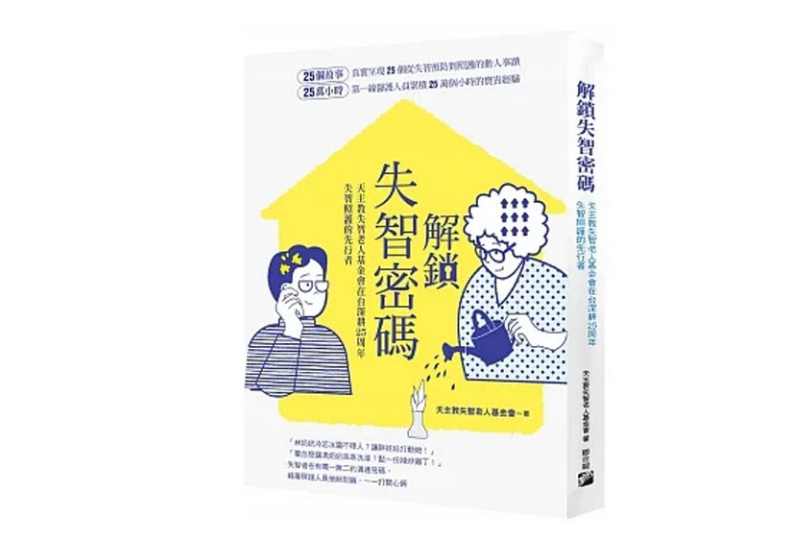
(本文作者為黃安琪、廖靜清,原文節錄自《解鎖失智密碼: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第一線醫護累積25萬小時的25個動人故事》/聯合報-健康事業部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