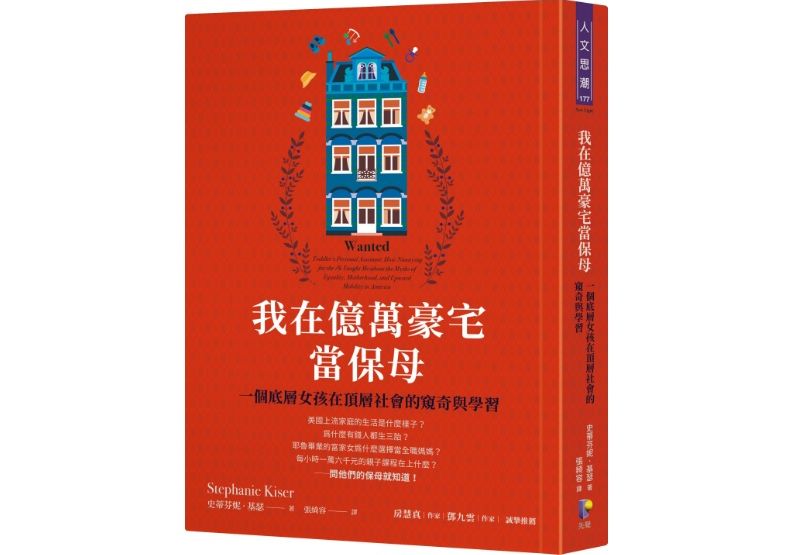美國上流家庭的生活是什麼樣子?耶魯畢業的富家女為什麼選擇當全職媽媽?——問他們的保母就知道!史蒂芬妮出生於社會底層,她從小被評估為「發展落後」,卻努力成為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沒想到,畢業後竟墜入學貸地獄。窮途末路的她,只好展開從未想過的職涯:幫紐約上東區富豪家庭帶小孩,擔任富N代幼兒的「私人特助」。但金錢能買到的東西、階級的現實、僱主家的精緻教養,都不斷刺痛著童年充滿陰影的史蒂芬妮。她也同時看見,即使是有錢人家裡高學歷、高成就的媽媽,也和普通家庭的媽媽一樣,面對著過多的要求、失衡的親職分工。這一切讓她陷入了迷惘──擁有金錢,就等於擁有幸福嗎?她應該繼續待在僱主家,還是放棄這份高收入,勇敢為自己的夢想去闖一闖?
傭人不用健身
只要大寶、二寶醒著,史蒂芬妮做什麼事情都需要我協助,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那年夏天,我大多早上 6 點 45 分上班、晚上 7 點半下班,雖然薪水很高,但工時很凶殘,比起我爸在工廠上班的日子,我的勞逸平衡也好不到哪裡去。
老公進城上班後,剩下史蒂芬妮二打一,她說自己沒辦法一次帶兩個。對我來說,帶小孩雖然很累,但至少不會一直鑽牛角尖,反正清醒的時間都在應付別人的需求。
等到我下班洗完澡,差不多都晚上八點了,我回到地下室的房間,打開電腦,查看一則又一則的「徵室友」廣告,看得我壓力好大。在紐約找房子,尤其是租金合理的房子,根本難如登天。
一看到有興趣的徵室友廣告,我就會傳個簡短的自我介紹過去,內容包括我的工作、我幾歲……等,都是一些沒趣的事,大家互相交換這些情報,彷彿真能就此判斷彼此適不適合當室友。
夏天的尾巴來得很沒勁。9 月勞動節長假,我們從漢普頓回到紐約。週六那天,三位老友來紐約幫我搬家,我的家具不多,一張床,一臺電視,衣服和鞋子也只有幾箱,我們只花了一個鐘頭的時間,就把所有家當從五層樓高的公寓扛到一樓,一件一件堆上從U-Haul租來的搬家卡車。婕思幫我搬完最後一箱之後,奧莉薇雅問我準備好了嗎?
看著空空如也的公寓,我完全認清自己過去自傷了一整年。憎恨多麼醜陋,我竟然任憑它支配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環顧四周:油漆剝落,水管外露,我心想:這公寓有夠破爛,就這樣搬走雖然難過,但也象徵我有機會重新來過。我一邊收拾包包,一邊看了看本來屬於萊菈的房間,正午的陽光從窗戶溜進來,灑在原本擺放床鋪的地方。未來還有好多好事在等我;我開始懂了。信心也更堅定了。
9 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是勞動節,隔天我回去上班,來到史蒂芬妮在翠貝卡的頂樓豪宅,雖然沒有漢普頓的避暑別墅那麼寬敞,但一樣漂亮。我跟MTV實境秀《比佛利拜金女》裡的蘿倫一起搭電梯上樓,她在垃圾桶旁邊停住腳步,扔了幾雙范倫鐵諾的鞋子進去,我後來把這些鞋子全都撿回來,雖然尺寸不合,但可以上網拍賣。我敢打包票:蘿倫肯定不曉得Poshmark這個二手交易平臺。
「早安,狄格比。」我說。「閉嘴。」他回我。幾秒鐘過後,史蒂芬妮來到廚房,把二寶交給我抱:「我需要換衣服,但先問問妳:搬家還順利嗎?」「很順利!超級輕鬆!而且我超愛我新租的房子,有露臺,有健身房,」想到這裡,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揚,「我想我會過得很開心。」
「什麼?健身房?」史蒂芬妮說。她的口氣帶著敵意,我聽過她這樣子跟別人說話,像是服務生、祕書,這些人不是只需要寒暄幾句,就是她自覺人家不如她。我上一次聽到她用這種語氣是在 8 月底,有工人來改建她的第二套廚房,工人問能不能用洗手間,但她拒絕了。「抱歉,你要不要開車去市中心上?市中心有一間星巴克, 10 分鐘的車程而已。」我雖然知道史蒂芬妮待人簡慢,但她從來沒有這樣對我過。「我們這裡前幾年才有健身房。妳倒是過起我們的生活來了。我們付妳的薪水是不是太高了?」她笑著說。

麻煩清洗內褲
狄格比 5 歲了,幾乎天天都大便在褲子上,而且他並非無心,而是居心不良。都已經訓練他用馬桶訓練了三年,他只挑方便的時候用,而且明明曉得大便在褲子上是不對的,卻還是照犯不誤,他媽一直叫我用手洗他沾到大便的內褲。
「他就是太聰明了,」史蒂芬妮嘆了口氣,我把一籃糊著屎的內褲拿進洗衣間,「他放不下手邊的事,實在離不開,疊樂高疊得太專注了,沒辦法停下來去用洗手間。」
我這整個星期都在面試新的職缺,史蒂芬妮渾然不覺,一旦有更好的機會,我立刻洗手不幹,她對她兒子的觀察實在錯得離譜,但我懶得理她了。
「這兩件可以直接丟了?」我一邊問,一邊看著沾滿(不是嬰幼兒而是)孩童大便的白色內褲。「當然不行。這些是亞麻內褲,妳知道一條多貴嗎?先在水槽裡浸一浸再刮掉。」我嘆了一口氣,但還是乖乖照做,如果還想每個星期領到薪水,就得謹遵老闆的要求,不論再怎麼扯都得遵守。我實在搞不懂,這位太太不久之前才誇耀自己的鞋子全是香奈兒,怎麼就買不起新的亞麻內褲給兒子呢?不過,我很清楚史蒂芬妮二號才不管我懂不懂。「媽媽!我還要浴鹽!」狄格比在浴缸裡大叫。
史蒂芬妮朝兒子飛奔而去,幫他倒更多浴鹽,再回來時,我拿著兩條內褲在水槽裡互搓,狄格比大完之後在大便上坐了一陣子,有些大便牢牢黏在內褲上,我希望用搓的搓下來。「妳在搞什麼?」史蒂芬妮衝著我吼道。我頓了一下,迷惑不解。「洗內褲啊?」「哎,好,內褲不是這樣洗的,我的媽啊,芬妮,妳要好好學怎麼洗才行。」史蒂芬妮抓起內褲,開始徒手把大便摳下來,摳了幾下之後,她把手一揮。「別在這裡礙事,去照顧二寶。這家裡的事情就是這樣,樣樣都得要我親自動手。」
「芬妮,我要妳跟狄格比好好培養感情,妳在這方面花的心力太少了,他到現在還是很排斥妳,所以呢,你們今天要一起共進午餐。」史蒂芬妮跟我說話的態度,彷彿當我是無能的小嬰兒,我們常常愈聊愈尷尬,我覺得她講話之所以那麼做作,是因為她一直想裝出得體的樣子,這感覺很像在跟AI機器人說話,但是史蒂芬妮是血肉之軀,無法拔掉插頭,更無法調低音量。
「好,沒問題。要帶他去哪裡吃午餐?」狄格比在房間聽見我們說話,立刻尖叫抗議。我跟露比和杭特單獨用餐過數 10 次,他們最愛Shake Shack漢堡店、麥當勞、披薩,還有他們家轉角的貝果店。狄格比的飲食禁忌雖然很多,但畢竟也才 5 歲,我猜想我們會去速食店、貝果店之類的—大白天就能吃到薯條,想一想真是誘人。
「我訂了 12 點的Fig & Olive,你們再過一個鐘頭就能出發了。」這下換我(在內心)尖叫了。Fig & Olive位在住宅區,會去光顧的都是穿西裝或鉛筆裙的專業人士,這間高檔餐廳提供當令的地中海飲食,帶位小姐滿臉困惑,安排我和狄格比坐在一桌律師隔壁,他們正在討論一樁複雜案件應該如何攻防。
「狄格比,需要我幫你問一下有沒有兒童餐嗎?」我問。我快速瀏覽了一下主菜—沒有一道我認得,狄格比的閱讀能力雖然很強,但應該看不懂有哪些菜色可以選吧?「我已經選好了。」「真的假的,」我很詫異,「你要點什麼?」「我要點日本南瓜燉飯,很好吃。」「聽起來很棒。」我說。想一想我跟狄格比一樣大的時候,我們家連生鮮雜貨都買不起。我就讀的公立學校有附免費早餐,需要的同學都會提早一個小時到學校,以免早餐被拿完。
狄格比雖然才 5 歲,對於點菜卻自信十足,甚至毫不考慮點兒童餐,這樣的傲慢和特權,就連在大人身上都很罕見,遑論 5 歲大的孩子。好不容易等到上菜,真是謝天謝地。跟狄格比共進午餐,簡直就像陪一個小老頭度過午後,儘管狄格比因為家裡保護得太好,還是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他有個老靈魂,既不會亂開玩笑,也不會吱吱咯咯笑個不停,缺少很多小孩應有的特質,我完全不曉得該怎麼跟他互動,加上他瞧不起我,相處起來更加困難。
「芬妮,」狄格比問:「我會不會快死了?」這問題嚇壞我了。「怎麼會?狄格比,你才 5 歲。」「5 歲也有可能得癌症。」這倒是沒錯,可是……我猶豫了一下。跟小朋友談生死話題—就算是跟我很要好的孩子—都必須字斟句酌。他們的心靈很脆弱,可能會誤解你話裡的意思,或者愈聽愈迷糊。「沒錯。但大部分的人都很長壽。我覺得你還用不著煩惱。」「可是,如果我吃太多糖,我的身體就會很虛弱,很虛弱就打不贏壞細菌。媽媽說人死了之後沒有天堂,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不過,聖誕節的時候,奶奶說耶穌會在天堂等我。」他重重嘆了一口氣,一點也不像 5 歲的小男生。
「我不想死。」雖然狄格比和我無望深交,但我替他感到難過。他還這麼小,就這麼特立獨行,這個也怕、那個也怕,從小就被他那寵溺小孩的媽媽灌輸了一堆恐懼,比起做母親,史蒂芬妮對於扮演完美媽媽更上心。狄格比沒有做自己的自由,也沒有形成自己想法的自由。雖然沒有「正確的」教養方法,但我認為過猶不及,如果不懂得節制,孩子就可能知道的太多(或者太少),下場就是變得像狄格比這樣。

那天下午,我提了離職
那天下午,我跟史蒂芬妮提了離職,並且打電話給仲介公司,讓他們知道我真的不做了,我的仲介在電話另一頭嘆了一口氣,說她一點也不意外。「為什麼?」我問。「我們上次介紹給史蒂芬妮的保母,還不如妳撐得久,那保母有一次外出吃午餐,就再也沒回去了,史蒂芬妮還以為保母被綁架或者遇害了,但保母說沒事,只是沒辦法再幫史蒂芬妮帶小孩,多帶一秒鐘都不行。」
麥迪遜仲介公司馬上幫我安排三場面試。第一場是來亂的,小朋友很煩,而且沒洗澡,我跟家長還沒聊完,就知道自己興趣缺缺。如果我還想在保母這一行混下去,就需要找到我心目中的完美家庭—父母和孩子都必須跟我合得來,而且認同我帶小孩的方法。這雖然很難,但有機會,重點是要有耐心。
我前往第二場面試,敲了敲公園大道的豪宅大門。仲介先幫我做了心理建設,說這家人非常有名:「行事務必謹慎,」仲介說:「這一家是重要的公眾人物。」我迫不及待想看一看究竟是什麼人。來應門的是黑髮男子,極富魅力,親切地跟我打招呼,他太太嬌小玲瓏,柔弱但是熱忱。我這輩子從來沒看過這對夫妻,他們的豪宅雖然像雜誌一樣漂亮,但卻沒有任何讓我熱血沸騰的地方。我原本幻想面試我的會是明星夫妻檔布蕾克.萊芙莉和萊恩.雷諾斯,沒想到就只是到另一戶有錢人家、坐一坐典雅的絨布沙發。
「可以問妳一個問題嗎?」黑髮男問。「當然可以。」「妳一點也……」他說到一半打住,想一想該怎麼說才對:「妳不太像其他我們面試過的保母。老實說,我覺得妳不適合。妳雖然樣樣都好,但我們在找的比較像女傭,我們的孩子都大了,只需要人家準備三餐和飯後清掃。但我還是很好奇,妳怎麼會想做這份工作?」我把我的處境解釋給他聽,包括學貸啦、利率啦,還有我怎麼誤打誤撞進入這一行。我忍不住覺得荒謬,我都還沒說自己通常不下廚、不清掃,但卻似乎也沒有說的必要,光是看我的外表,他就推斷我肯定不願意。
我忍不住納悶:如果坐在這裡面試的,是跟我同年紀但不同族裔的女生,情況會怎麼樣?直接被認定是當女傭的料嗎?「但我好愛我第一次帶的寶寶,每天都高高興興去上班。我想我察覺自己愛上了這份工作。」送我離開時,這對夫妻跟我漫不經心地閒聊,看著他們,我想起了紗夏和她老公,雖然身處榮華富貴,舉止卻與常人無異。他們帶我走過長長的走廊,我瞥見牆上有一幅巨大的全家福,裡面有一張熟面孔,我一踏出門外,立刻掏出手機Google。儘管我不會把伊凡卡.川普的小姑歸類為名人,但仲介或許只是慎重其事,無論實情如何,我都很氣自己—我竟然對這對夫妻心生好感。
我搭地鐵到下城區參加當天最後一場面試。時近傍晚,太陽快下山了,翠貝卡的石子路沾染了夕陽餘暉的煦煦流光,雜誌說翠貝卡區格林威治街四四三號是全紐約最能「防狗仔偷拍的豪宅」,住在這裡的都是赫赫名流和超級富豪,面試我的這戶人家雖然並非名人,但鄰居全都大有來頭。
豪宅的接待大廳昏暗舒適,門房之殷勤周到,勝過公園大道的頂級門房,但我猜不殷勤也不行,他們看守的住戶,可是大賈斯汀、珍妮佛.勞倫斯這些大有來頭的人物。「先生和太太還沒回來,」門房向我解釋:「您可以先在大廳等候。」我坐在燈光朦朧的大廳裡,感覺坐了好久好久,突然靈光一閃:怎麼紐約市所謂的「酷」和「潮」,都是昏暗昏暗的,真是奇怪了?
我看了一下時間。表定 4 點半面試,現在都已經 5 點 15 分了。換作是我遲到那麼久,大概早就直接被刷掉了。他們這樣拖拖拉拉令我發愁,都還沒見過面,就覺得我可有可無。「史蒂芬妮?」其中一位門房呼喚我:「太太剛剛打來,說他們塞在路上了,但我們先送妳上去,奶媽蘿莎在樓上,她會用FaceTime讓妳面試。」雖然很詭異,但我恭敬不如從命,反正也沒有其他辦法。門房陪我去搭電梯,幫我按好樓層,以免我不小心晃到其他名人的住家去。
蘿莎是上週末班的奶媽,全職管家親切體貼接待著週日來訪的我。蘿莎說駱博士和先生帶兩個大的去布朗克斯動物園玩,司機找不到更快的路線趕回來,但小寶寶在家,我FaceTime面試結束之後,她很樂意帶我參觀一下。「這給妳,」蘿莎把畫面開好遞給我,「他們會打這支,這是我的公司機。」
公司機?這裡又不是Google總部?我們只不過是坐在人家 140 坪的房子裡啊?但我環顧四周,看一看這裡僱用的人,或許是我想錯了,在這裡持家跟經營企業沒兩樣,兩者都需要員工。僱用一個人,跟僱用十個人,完全是兩回事。終於等到駱博士打來,我等得滿肚子氣,加上面試了一整天,又跟一堆陌生人說話,實在已經很累了,我以為通話會草草結束,沒想到我們卻很聊得來,才聊不到幾句,我就喜歡上駱博士,駱博士似乎也覺得我這個人很有意思。
「我們一直在找像妳這樣的保母。」面試開始不久她就這麼說,我深思熟慮回答她每一道問題,不時開開玩笑,而且都有戳中笑點。我很難得跟人一拍即合,她邀我下星期來跟他們全家一起相處,這讓我精神為之一振。我向她道謝,離開的路上,我回想剛才的對話,我很喜歡駱博士,我們的育兒哲學顯然很像,她跟她先生都有重要的事業要忙,沒辦法親力親為帶孩子,她坦承自己需要全天候保母,年紀要輕,體力要夠,必須上滿核心時數——每天早上 7 點到晚上 7 點半,我會需要出差(常常還得出國),負責管理其他參與育兒的員工。
我自知做得來,但我才剛走出史蒂芬妮煉獄,很猶豫要不要再投入這麼高強度的工作。我刷了MetroCard進入地鐵站,手機突然響了。「史蒂芬妮!」女仲介尖著嗓子說道:「駱博士很喜歡妳!她知道妳今天還去其他家面試,她不希望妳被搶走,所以打電話來開了價碼,希望妳狠不下心拒絕!」「多少?」「4 百萬,加上醫保、MetroCard儲值、年終獎金,加班工資加倍。妳覺得怎麼樣?」我刷出地鐵站走回大街上,眼前是難以置信的七位數高薪,我不確定自己該不該接。
我最近才開始提升自我,我現在做的任何決定——接下什麼工作、服務哪戶人家,都會長遠影響我接下來的發展。我站在紐約街頭,面前是我來紐約所夢寐以求的高薪——這個價碼簡直再好也沒有,我一口氣站上食物鏈頂端,穩坐全紐約最高薪的保母,短短幾年就登峰造極,既坐擁高薪,又能展望高額年終,還有做夢也想不到的福利,但怎麼覺得怪怪的?
我不想拒絕這樣的大好機會,但又還沒弄清楚自己還沒準備好的理由,所以我回了「可以」。我預定一週後到駱博士家上工,但我對這項抉擇依然不放心,因此,我答應到上城區參加最後一場面試。雖然我主要都透過仲介來找僱主,但偶爾還是會上Care.com看看,最近跟一戶上東區的家庭聯絡上,家中有兩名幼兒,誠徵年輕、活潑、精力充沛的全職保母,照理來說,這些資格我全部符合,但我最近常常腰痠背痛,真的很想休息,不過我沒有在簡訊中提到這些。
面試當天早上,我差一點就按下取消,反正這家人不可能開出比駱博士更好的待遇,但我一直拖著沒打電話,害怕雙方會起衝突,最後決定還是乖乖去面試比較好。「嗨!」希奧來應門,用氣音跟我打招呼:「寶寶在睡覺。進來客廳吧。」黛凡和希奧比我想的還要年輕,都才 30 多歲,臉上皺紋不多,眼底還有光采。
希奧穿著Nike的Air Force鞋,黛凡的穿搭亮點我想不起來,只記得我當時心想:他們跟我認識的上東區家長很不一樣。從他們的高樓豪宅看出去,可以飽覽整個紐約的風景,行人像小蟲子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移動。人在紐約很容易覺得自己很渺小,但站在高樓往下看,整個紐約變得好迷你。
「這是我的小芭比娃娃—小芭,然後這是我的大芭比娃娃—大芭。」他們 3 歲大的女兒小蕾向我解釋。她秀給我看各式各樣的娃娃,我觀察到小蕾雖然很外向、但很認真,雖然聰明、但或許有一點跋扈。露比 3 歲的時候雖然事事好奇、但個性矜持含蓄,小蕾則很愛聊天,東問西問問不停,就連坐著都不安分,一直扭來扭去,她爸媽請她讓大人好好說話,她雖然不滿,但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玩具上,暫時不理我們了。
「不得不說,見到妳我們很興奮。」這聽起來像所有面試的起手式,接下來的 20 分鐘也沒出什麼差錯,我神色自若回答他們的問題。面試了這麼多戶人家,我已經學會該如何應對進退,而不是只有自我推銷、自吹自擂。剛開始雖然有些尷尬(面試大多都是這樣),但感覺很自在,我回想上次在工作場合這麼放鬆是什麼時候?好像就是在紗夏家的那段時光。
我謝謝黛凡和希奧撥冗跟我碰面,小蕾問我會不會很快再去她家玩?我們三個大人都笑了,我跟她說應該會喔,但卻暗暗覺得我一定會再回來。搭乘地鐵Q線回家的路上,我回想了一下工作細節,工時依然很長(早上 8 點到晚上 7 點),夫妻倆都是律師,黛凡常常出差,因此需要配合度高的保母,尤其他們還考慮要生第三胎。他們不像駱博士請了大批管家,所以家裡只有寶寶和我,我雖然知道怎麼對付 3 歲和 1 歲的小孩,但我只跟全職媽媽搭檔過,而且當時還有管家幫忙,因此,我很懷疑自己忙不忙得過來。
隔天,我走去世貿中心找朋友,走到一半,手機響了,黛凡問我願不願意接工作,待遇很優渥,但是不含醫保,而我已經不能再請我爸媽幫我加保了。「不勝感激,」我告訴黛凡:「給我幾天的時間考慮一下。」走到下城區後,我寫信給幫我和駱博士牽線的仲介:我再過幾天就要上工了,合約至今還沒收到,我需要先檢視合約才可以開始正式工作。仲介馬上回信,說她跟駱博士講了合約的事,但駱博士真的很忙,等我上工之後再把合約給我。我轉頭把這件事告訴朋友,告訴她我覺得聽起來不妙。過了幾天,我打電話給黛凡,告訴她我準備好隨時上工。
(本文節錄自《我在億萬豪宅當保母:一個底層女孩在頂層社會的窺奇與學習》一書,作者史蒂芬妮.基瑟,譯者張綺容,先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