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僅為情境配圖)
在父母的家中確保自己的空間
協助母親度過晚年的,除了伴侶小滿以外,還有住在斜對面的鄰居一家和幫傭。住在斜對面的鄰居一家,太太跟我同年,丈夫年紀稍長一點。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們的三個小孩都長大成人了。
他們剛搬來的時候,孩子都還小,常常跑來母親家玩。等他們長大成人後,也常跟雙親一起來關心母親的健康狀況。母親稱呼他們是「地方家族」,現在兩家也還互有交流。
母親把家中的鑰匙交給他們,舉凡照顧貓咪和其他事情都有勞他們幫忙。以前母親還有辦法外出工作時,他們也會在冬天先幫母親把房間暖氣開好。多虧有這一家人協助,母親才能在家中生活到最後一刻,我始終很感謝他們。
我們請了好幾個幫傭,其中有兩個人跟我們相交特別久。這兩位幫傭是阿德女士還沒離開時,我們申請看護保險認識的,後來母親請他們來照顧自己。他們都很溫柔,工作也認真賣力,將母親交給他們照顧我很放心。
自從母親接受看護保險後,也有別的幫傭來幫忙。比起長年相處的那兩個人,交情自然是淡了一點。雖然相交的時間不長,他們還是有來好好照顧母親,這份安心感十分重要,母親得以在家中安然生活,他們功不可沒,我很感謝他們。
每次想起有這麼多人合力支援母親,我就會反思自己這個女兒做了些什麼。我在45歲時離開服務22年的醫院,那一年母親77歲,也就是她去世的三年前。老實說,我在辭職之前過著長時間勞動的生活,一直沒有多餘的心力去關照母親。
等我真有時間去照顧母親,老實說我倒是有些彆扭。我自認跟母親還算合得來,但我們這對母女畢竟有20年以上沒有日常性的交流了。
說穿了,我是基於母親的健康問題才不得不返家相聚的。母親本人也不願意這樣,因此我們無論如何都會費心顧慮對方。
母親身體狀況好時,我們的對談歡快熱絡;母親狀況不好時,光是陪伴她都是件很辛苦的差事。例如整理藥品、幫她洗澡、洗衣服、買東西,該做的事情不勝枚舉,過去有具體工作的時候反而還比較輕鬆。
如果要我回到過去,我會想辦法在那個家裡尋找自己的空間。抽空去照顧別人的時候,確保空閒時有自己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的切身體會。
甚至不需要一個完整的房間,只要能夠互相保有一點隱私的空間就夠了。這樣在看護的過程中也可以放鬆一下。
父母需要幫傭更勝子女
到頭來,真正幫助母親的是小滿、鄰居一家,還有諸位幫傭,也就是沒血緣關係的人。尤其會按照約定來照顧母親的幫傭,真的居功厥偉。母親曾經坦白地告訴我,比起我這個靠不住的女兒,她寧可希望幫傭來照顧自己。
我從事護理工作時,也常聽到患者這麼說。果然做父母的都有這種想法,因此我立刻表示諒解。
「跟出於好意的親人比起來,來工作的幫傭還比較好相處一點,這樣很多事情也不用費心顧慮對方。」
「子女說『有空就會來』最令我困擾了,因為在我需要的時候,他們絕對不會來。」
這是某一位患者說的,他很想請幫傭來照顧自己,家人卻始終不肯答應。照理說請幫傭也能減輕家人的負擔,但他們說什麼也不想讓外人進到家裡。
我對於接納外人沒有抵抗感,所以當我認清自己無法代替幫傭,便果斷地請幫傭回來照顧母親。我明白自己應該出去工作,提供經濟上的支援,好讓母親可以多請幾個幫傭。
顯然這也是母親的期望,現在我依然認同,孝道有各式各樣的實踐形式。母親想要的,是她個人聘請的幫傭。雖然所有幫傭都是自費的,當然會產生經濟上的負擔,但我們能夠輕鬆傳達自己的需求。
只是,幫傭的關照終究有其極限。父母有小孩的話,有些事情還是必須由小孩處理。好比決定母親的治療方針,就是我的首要之務。母親個人的意願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也需要一個中間人來替她簡單說明病情,引導她提供答覆。
另外母親還有小滿這位伴侶,他們並非法定夫妻,小滿沒有法律上的決定權。我要考量母親的意願和小滿的心情再做出決定,我認為這才是我的職責。
如今回過頭來看,「地緣更勝血緣」的人際關係支持著母親,她才得以安享這種符合自己信念的晚年生活。這對我們母女倆來說,都是最舒心的形式。能夠支援母親的生活方式,我非常滿足。
另一方面,看護保險制度的目標,在於社會化的看護制度。但在有家人的情況下,如果家人不願意伸出援手,看護也是無法成立的。在這個社會成本有增無減的時代,我們再怎麼希望政府充實看護制度,也只是緣木求魚罷了。不過,以這樣的現狀迎接未來是否妥當呢?送別母親之後,我一直在深思這個問題。若沒有聘請自費的幫傭,我也不會有現在的滿足感吧......。一想到那些忙著照顧血親的人有多辛苦,我也不免悲從中來。
(原文刊載於宮子梓《行前整理》/時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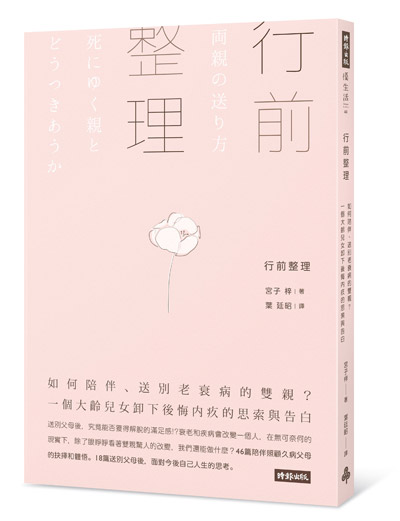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