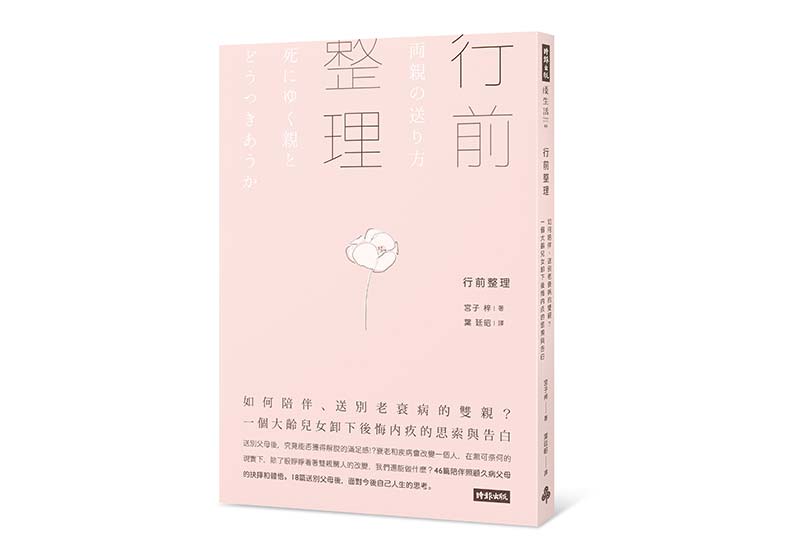從害怕雙親死亡的恐懼中解脫
父親與母親的忌日都在四月,父親是15日,母親是17日。他們稱不上是圓滿融洽的夫妻,但忌日只差了兩天而已。每到櫻花盛開的季節,我就會想起送別雙親的回憶。他們都是在三月中旬病況惡化,於櫻花紛飛的時期陷入病危的狀態。
關照二位家老的醫院就在飯田橋車站附近,從我們家附近的吉祥寺車站搭乘中央線,在市谷車站到飯田橋車站之間,可以從窗戶看到河畔邊的櫻花。
過去我每天看著盛開的櫻花,思考父母離開的日子不遠了。那是一段揪心的日子,每次看到櫻花,我就會想起那段痛苦的時期。那一陣子我每天都要有心理準備他們可能再也無法康復;我隨時都提心吊膽,不曉得那一天什麼時候到來。
那種膽戰心驚的日子真的很痛苦,所以父母去世的那一刻,我確實有品嚐到一股解放的滋味。然後還有一種果不其然的心情,父母去世的日子終究還是來臨了。
我見過許多患者死亡,對那些哀痛莫名的家屬來說,死亡也是一種解脫吧,好幾次我都有同樣的想法。來說一段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吧,曾經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死於肺癌。他跟年紀相近的妻子感情融洽,膝下有兩個就讀高中的兒子。兩位愛子仰慕父親的景象,我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
後來男子的病情惡化,妻子也住在病房裡,跟兩個兒子輪流照顧他。男子病逝後,大家哭得很傷心,他們確實是感情良好的家庭。相關處理告一段落後,那位妻子在整理行囊時,感嘆這一切終於結束了。兩位小孩也說等葬禮結束後,就能參加社團活動,順便跟朋友相約去玩了。
聽到他們的對話,我心想這些人盡心盡力,如今總算獲得解脫了。他們再也不必擔心自己心愛的人什麼時候會死去了,最痛苦的那一刻已經結束了。
然而,身處激流之中,是沒辦法這樣思考的。當下的痛苦彷彿永無止盡,就連我也不例外。那麼,是不是應該有人提醒他們,痛苦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呢?我是有這麼想過,但我還是說不出口,畢竟那是有失厚道的事情。
父母去世後,我們就從失去父母的恐懼中解脫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消說,我們不是討厭恐懼才希望父母去世,正因為我們不想失去父母,才害怕死亡。死亡會喚醒我們許多複雜的情感。
父母一死,子女不再受權威束縛
母親去世後過了一段時間,我又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不受父母束縛這件事。我內心湧現一種情緒,自己再也無法依賴父母了,接下來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
母親對我的思維有強烈的影響。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母親的女兒,現在也不會這樣過活吧。打個比方,這就好像被強烈的磁場吸引,而不是染上母親的色彩。母親的磁場很強烈,說不定我自己也帶有什麼磁性吧。
說穿了,我的人生深受母親的影響,對此我並沒有怨恨母親。幸運的是,我甚至覺得這種人生也沒什麼不好。只是,若有人問我是否想再次成為父母的女兒,我恐怕無法馬上給予肯定的答覆。
要知道我們的家庭很有可能破裂,還好以前幸運地克服了難關,但下一次誰也不敢保證有同樣的幸運。一想到這裡,我只能說滿足現狀不代表我就願意重來一次。
個性再怎麼契合的親子,父母對孩子來說都有絕對的權威。是母親的話語,讓我意識到這一點的。那時候我還是小學生,有一次我說,媽媽跟我是好朋友。結果母親氣得破口大罵,她說親子永遠不會是朋友,父母對小孩來說就是權威。我以為母親會認同我,因此對她的回答感到很震驚。不過,這件事也印證了我們日後的母女關係。基本上母親對我頗為民主,但親子之間依舊潛藏著上下關係。
我猜母親不想欺騙我,佯裝感情良好的模樣吧,這當中很有母親的誠實風範。她常對我說,「我是32歲生下妳的,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頂多50年,親子關係有這麼長就夠了。父母終究是權威,得在適當的時機消失才行。像我一樣有了年紀再來生小孩比較好,年輕時產子的話,親子關係太漫長了。」32歲算晚產,這也稱得上時代的變化吧。
我是昭和38年(1963年)出生,在那個年代32歲才生產算很晚了。當時的平均結婚年齡,男性是27歲,女性是24歲。光看第一胎的平均年齡,最古老的資料是昭和50年(1975年),平均為25歲。平均年齡超過30歲,是平成23年(2011年)的事了。
母親開始真正變老後,就沒再說過類似的話了。這與其說是她想法改變,不如說是她不想死的心情更強了。母親這種逗趣的部分,我也非常喜歡。
我49歲那一年,母親去世了。雖說是偶然,但我們相處的時間真的被她說中了。
(原文刊載於宮子梓《行前整理》/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