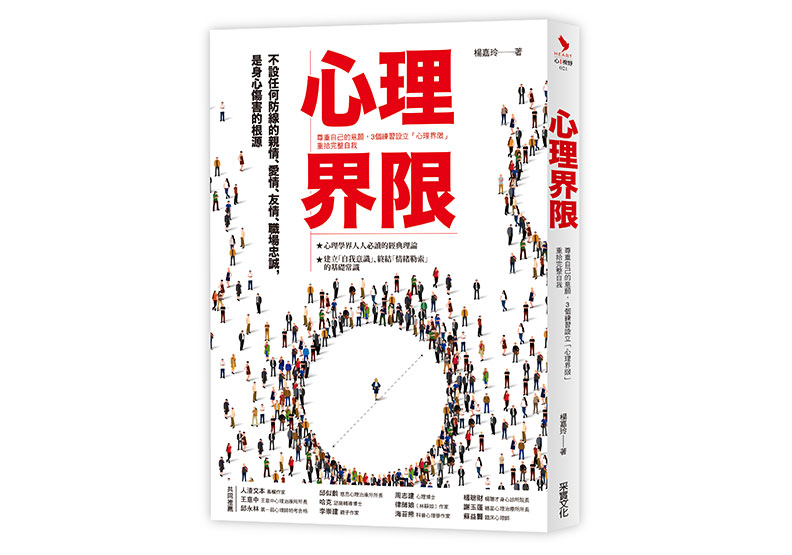從妍熙小時候開始,她的父母總為了錢吵架,每回爭執結束,爸爸就會跑出去喝酒,媽媽則是會開始哭訴自己遇人不淑,最後拉著妍熙說:「妳那沒有用的爸爸,我是不可能再依靠了。妳一定要認真念書,媽媽將來就指望妳了。」
抱怨的話聽多了,妍熙也開始討厭爸爸,把爸爸當做陌生人,惹得爸爸更為生氣,常常借酒裝瘋。妍熙受夠了爸爸的無理取鬧,發誓將來長大一定要讓媽媽過上好日子。就這樣妍熙硬生生把自己卡進父母的婚姻關係中,漸漸地和母親同盟、父親疏離,把家庭的重擔攬在自己身上。
不管妍熙做得再多,媽媽的抱怨從來就沒有減少。小時候,妍熙興沖沖地拿著一百分考卷回家,結果媽媽非但沒有讚美她,反而酸言酸語:「會念書又怎樣,將來嫁人,還不是只能在家裡做牛做馬。」讓妍熙非常挫折。
長大之後,妍熙努力工作,存錢帶著媽媽出國度假,結果媽媽一路嫌東嫌西,批評她浪費錢。妍熙試遍各種方法,始終無法讓母親覺得滿意。每次回家,媽媽只會一直找她碎唸爸爸又幹了什麼好事,一定是上輩子欠他太多,這輩子才會這麼辛苦。
不管妍熙怎麼苦勸,媽媽總是有一套自己的說詞。妍熙若表現得不耐煩,媽媽就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我辛辛苦苦把妳養得這麼大,不找妳說,我找誰。」讓妍熙覺得愧疚,怎麼連聽媽媽說話這麼簡單的小事都做不到。
後來妍熙決定追求自己的愛情,可是不論她帶什麼樣的男朋友回家,媽媽總是說:「這個男人配不上妳,妳不要被甜言蜜語給騙了。」
有一次,妍熙受不了,對著母親吼:「我怎麼挑,妳都有意見,到底談戀愛的人是妳,還是我?」訝異的母親略顯示弱地說:「我只是好心提醒妳,不要步上我的後塵,嫁一個沒前途的男人,到最後吃苦的人是妳。」
即使知道這些話不全然是真的,妍熙就是無法違逆母親的意思。以至於她一再地錯過適合的對象,也錯失了適婚的年齡。最後,她終生不婚,成為媽媽唯一的依靠。一句:「媽媽只剩下妳了,妳千萬別讓我失望。」成為妍熙丟不掉的包袱。
透過這個例子,你可以很清楚得看見,一個失功能的丈夫是怎麼造就一個寂寞的媽媽、一個痛苦的孩子,以及一整個失衡的家庭。
從家庭治療學派的觀點來看,妍熙承接了父親應該扮演的角色,讓自己成為母親的「情緒配偶」,也就是一種「情感性小大人」的類型,這類型的人過度將自己的情緒與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融合,取代了爸爸或媽媽原有的配偶角色,成為他們的情緒伴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慰藉。
如同妍熙的媽媽,因為對自己丈夫失望,轉而向妍熙尋求情感上的支持,以淡化自己在婚姻裡的孤單感。然而,一個缺席的父親,勢必會造成一個焦慮的媽媽,她必須重新將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不然會失去心理平衡。
尚未有分辨能力的孩子,在沒有長大之前,就被賦予如此重要的任務,不知不覺接受了媽媽的暗示,認同了爸爸的無能與媽媽的無奈,成為父母婚姻裡的第三者,心理發展與人際關係,當然會受到影響。故事中的妍熙,首當其衝的是,她很難對媽媽以外的人,培養出真正的親密與親近,心裡隨時準備好回家遞補那個缺席者的位置。於是,就算後來有機會成立自己的家庭,她所選擇的伴侶,又複製這樣的關係模式,成為被冷落、忽略的一方。
同時,你也會發現在情感型小大人的親子關係裡,「情緒勒索」是經常出現的戲碼。因為當事人過度與父母親其中一方情緒融合,也因此,只要爸媽在言詞上,稍微嚴厲或壓迫(例如:「我養你這麼大,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呢!」),他們就覺得難以承受,覺得自己必須滿足父母的需要,否則就會有愧疚感。他們經常是以爸媽看待自己的態度來認定個人的價值,很難有健全的自我概念,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對待的。因此,他們的心理界限往往是很模糊且脆弱的,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決定。
他們在生活中會不斷地交出控制權,以換得他人的認同感(特別是權威者:父親、母親、老闆、老師),也就是「綁匪」和「肉票」的關係。換言之,「情緒勒索」和「心理界限」經常相伴而生。情緒勒索要能成立,被勒索的一方往往是很難對勒索者,明確地說出自己的原則並堅持到底。反過來,一個人若很清楚自己要什麼,不能接受什麼,就算別人威脅、恐嚇、情感逼迫,也能難讓他改變動搖。
值得注意的是,習慣界限被侵犯的人,有朝一日,成為有權力者,一反手很可能也變成勒索者,用同樣的情緒創造對方的愧疚感,讓他人覺得不管怎麼做,他都有意見。即使有能力改變也不願意行動,情願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他們複製了上一代的行為模式到自己的關係中,無形中變成了自己當初最討厭的人。從此這樣的處理模式就被固定下來,變成一種難以打破的鏈鎖反應,不停在世代間傳承、複製,也就是所謂的「家庭魔咒」。
父母的情緒配偶的迷思:只要我再努力一點,我就能改變他
你在妍熙身上可以感覺到一股力量,默默地推著她走向拯救者的位置,即使她知道再付出下去,情況並不會好轉,但是她仍舊無法擺脫宿命的輪迴。
心理學家卡普曼(Karpman)博士發現,人與人的互動經常會重複出現沒有明說的心理遊戲,而幾乎所有的心理遊戲都會有:迫害者、拯救者和受害者這三個角色,他把這個現象稱之為「卡普曼戲劇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人們在三角形裡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會隨著不同的狀態不停地輪換位置。
最常見的互動就是受害者向拯救者尋求支持,拯救者伸出援手,激怒了迫害者,讓他變本加厲地傷害受害者,或者遷怒於拯救者。此時,原本的拯救者有可能就會變成受害者,而受害者也可能反過來調解,變成了拯救者。
就像在我們在這裡舉的故事,媽媽把滿腹的委屈向妍熙傾訴,妍熙認同了媽媽的可憐,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事情保護媽媽:一起指責爸爸的不是、故意說一些話刺激爸爸、不給爸爸好臉色。而爸爸感受到被排擠之後,覺得父親的權威受到挑戰,只好更用力地管教小孩,結果造成親子間更大的隔閡。
不幸的是,當妍熙自認為在幫媽媽出一口氣,一起抵制爸爸的荒唐,她就無法去看見,爸爸身為一個男人的壓力與痛苦,他被社會期待賺取足夠的金錢養家,若沒有達到標準,就會被老婆嫌棄、小孩也看不起他。在扮演加害者的同時,他的面具底下藏著深深的挫敗感,是不折不扣的性別受害者。
而那個看似最無助可憐的媽媽,在不斷地把苦水倒給小孩的同時,其實也扼殺了孩子的快樂,壓迫孩子一夕長大,好讓自己得以依靠,繼續當一個依賴者。她是婚姻裡的受害者,也是不停向孩子索討的加害人。
換言之,如果妍熙沒有看懂這整個模式,她就會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改變爸媽。也許是更加地努力,拯救媽媽離開這段婚姻,或是不斷地挑釁父親,告訴他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爸爸、好先生。當她陷入這段三角關係中,她就會想要控制,改變局勢,卻忘了爸媽的婚姻問題並不是她的責任,也不是她身為女兒的位置能改變的事,一心一意投入的結果,很可能到最後變成了烈士。
無論妍熙再怎麼努力,媽媽和女兒的相處關係裡是不會感覺到快樂的,即使媽媽嘴上對爸爸有再多的不滿,內心真正渴望的還是擁有一個疼愛她的丈夫。妍熙是不可能取代父親的位置,只能做一個永遠無法扶正的小三。同時,妍熙的允許與縱容,也會讓母親有了同盟的錯覺,認定了:「自己沒有錯,一切都是那個男人造成的。」而不用面對自己的責任,負擔起改變的義務。
沒有人可以改變任何人,除非當事人自己願意。不管你的出發點有多良善,只要對方不是發自內心的調整,當情況和他想得不一樣的時候,他就會把責任丟給你,認為是你的錯。
(本文作者為諮商心理師。原文刊載於楊嘉玲《心理界限》一書/采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