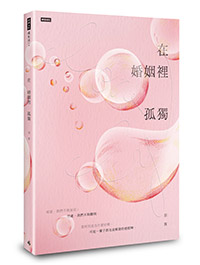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孩子睡了,我正在滑手機,檢查白天自己一個人在家時寫好的稿子。先生坐在我旁邊,也在玩手機遊戲,轉頭看他又想起我一天的行程,我突然有感而發:「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話說出口的時候還是有片刻的掙扎,就算這句話已經不是第一次說了,但是每一次想說出這句話時都可以感覺到,有什麼東西, 似乎正試圖要拉住我。
我清楚意識到它的阻礙,然後刻意地擺脫,把這句話說出來。跟之前每次聽到這句話的反應一樣,先生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微笑,手伸過來握了一下我的手,最後又回到手機遊戲裡。
我解釋了一下為什麼我會覺得幸福,主要是因為我過著在家接案的生活,可以不用通勤,免去辦公室的勾心鬥角和比賽加班的職場文化,雖然收入較低,但我擁有的是時間,對有小孩的媽媽來說時間何其珍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讓自己在面對家人的時候, 態度能夠保持從容。
疲勞和壓力都是讓情緒容易爆炸的原因,很多時候讓人神經斷線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身體因為不堪負荷而發出的警訊,我很幸運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還是可以選擇比較適合自己的工作型態, 而免於疲勞和壓力過大,造成面對家人時無法拿出耐性的情形。
那應該是個人的選擇,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去冒險,但是在工作期間體會到的,覺得自己累到隨時會情緒失控的那種不安,內疚於無法用笑容回應有好多事想跟媽媽說的小孩,對我個人來說,比職涯中斷的壓力更難以承受。
而我因為現在的選擇而感到幸福,就這麼跟先生說了。說出口時的掙扎猶豫,我想,是因為總有一種聲音在暗示我,不應該讓對方知道吧。
自己過得很好,對生活感到滿意,對他的付出也心存感激,這一切,好像是不應該讓對方知道的事。
會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我從小看見的婚姻樣貌,還是以彼此埋怨的居多,朋友之間似乎也不是只有我是如此,在臉書開始流行,無形中推動一種目標是讓人羨慕的放閃文化之前,我們其實比較習慣看到伴侶彼此埋怨,好像親密關係發展到最後,相知相惜是少數,抱怨說不完才是常態。
—已經過的很好了還不知道感謝。
—回到家也從來不幫忙任何家事。
—別人對他 / 她的好都當作理所當然......
看慣了婚姻生活就是報憂不報喜,在我心裡不斷累積,久了也沉澱出一個印象,所謂夫妻,就是不斷埋怨彼此,把結婚照上兩個人的幸福甜蜜,硬生生地變成一副諷刺的漫畫。
很多都不是半開玩笑的埋怨,而是真實地覺得對方占了自己便宜,覺得在婚姻裡是「自己在犧牲」,為了家庭自己已經非常努力付出,對方卻從未感到滿足。
不去檢視那些具體細節的話,會發現人跟人之間的抱怨總是如出一轍,好像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付出較多、得到較少,好像這也是一種關係中的弔詭,兩個人都在犧牲,卻沒有人因此感到幸福。
資深的已婚者總是會說,「婚姻都是這樣」,表面上和平而內在彼此嫌棄,暗自覺得自己值得「更好的婚姻生活」。會彼此感謝、沒有外人在場時依然相視微笑的夫妻,好像是戲劇裡才有的少數。
結婚時我們多半想著自己不會變成那個樣子,想要結婚時感到的幸福持續到永遠,卻很奇怪地,總是覺得埋怨的話比較容易說出口,好像當年長輩對我們說那些話,只是想提醒孩子以後不要跟自己一樣,卻總是提醒的越多,結果越是同樣的複製。
我在發現自己很難開口稱讚先生時覺得很驚訝,因為戀愛的時候我們並不是這個樣子,我對他有某種崇拜,覺得他比我堅強,特別喜歡那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感覺。
曾經有朋友向我轉述,說他從另一個女性朋友那裡聽說,在我跟她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我一直在說自己的男朋友對我多好,讓我多麼感動,而我竟然絲毫沒有察覺自己一直放閃,還自以為是低調的人。
可見得人的行為總是和自己以為的不同,留給別人的印象更是自己無法完全掌握,但這表示我不是向來喜歡埋怨另一半,婚後卻好像總是有個警鈴在大腦裡,隨時提醒我「不要把對方說得太好」, 尤其是當著對方面的時候。
當我覺得自己幸福而想要說出口時,就會想起聽過無數次的伴侶的私下埋怨:都讓他 / 她過得那麼好了......
那給我的感覺是千萬不要當面稱讚對方,也不要讚美自己現在的生活,否則對方生氣或吵架時就會理直氣壯地說:「都已經讓妳過得那麼好了。」
我發現自己是在害怕落人口實,好像我要是現在說了,謝謝你讓我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謝謝你的協助和包容,就會讓對方因為被讚美而得意忘形,也會讓自己在還有別的要求時,會被說成「太過貪心」而失去立場。
只是有這種感覺時,心裡也開始懷疑,如果我開口也總是那些提醒對方、埋怨對方沒做的事,那跟那些沒辦法欣賞彼此、也從不向對方道謝的夫妻有什麼不同呢?
埋怨彼此可能只是想找情緒的出口,但沒有人喜歡被批評或抱怨,或許我們都只是害怕自己受傷害,所以採取了和良好溝通背道而馳的對話方式:只強調自己沒有得到的部分,而視對方的付出為理所當然。
反省之後,我開始調整自己和對方說話的習慣,逐漸發展出來一套新的溝通原則:感到幸福時,當下就要說,而且最好是直接告訴對方。
一開始很不習慣,但是努力說出「覺得自己很幸福」的時候, 總會看到對方微笑了。
心情不好的時候,睡不著也要去睡。
相反地,如果對生活感到不滿、不快樂,甚至是無法停止的覺得自己「不幸」,可以先去睡一覺,隔天起來再說。
雖然隔天再說聽起來有點像在翻舊帳,但事實是通常起床後的隔天就會覺得事情沒那麼糟,我總是會在那時候恍然大悟,人的情緒,不管自認為多灑脫豁達的人,依然就像鑽牛角尖一樣,是越想就越走不出來。
這種時候並不適合溝通,最適合的事情是睡覺,讓自己身體休息心情也隨之平復,才能用冷靜的、不意圖傷害他人的態度討論問題該怎麼解決。
人會被當下的情緒所影響,放大對某件事情的觀感和好惡,這是我在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的《誰說人是理性的》當中看到的。人其實不像自己以為或想像的那麼理性,總是受到當下的情緒或感受所操控。
書中有一段讓我印象深刻的討論,雖然已經不確定作者所舉例的細節,但我做的筆記是,人會基於當下的情緒做出某個行為,但等到當下的情緒過了,就會忘懷情緒在當中的作用。而人總是認為「我當時會那麼做,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就把當時的決定合理化,甚至把它變成一個習慣而延續下來。
舉例來說,你可能在上了一天班,身體非常疲累的時候,看見家裡一團亂,對於提早下班,卻沒有動手整理的伴侶感到非常惱怒。因為這樣不想回應對方的親密,也不想來個晚安吻就直接去睡,隔天雖然沒有昨天那種情緒狀態,但晚上的晚安吻習慣,卻可能從此取消了。
我們通常不會記得自己因為身體勞累,所以情緒不佳的事情, 也會縮小甚至否認這件事情對決策的影響力,情緒會過去,當時的決定—取消晚安吻—卻可能延續下來。
因為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決定都是有道理的, 跟對方吵架是因為對方讓我們「忍無可忍」,不跟對方親密是因為「對方做錯了某件事情」,但很有可能,我們是在這種事後的合理化過程中,縮小了自己情緒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我們會忘記或否認自己其實可能並不理性,用事後蒐集線索、填補空缺的方式來說服自己:事出必有因,而我一直都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事情究竟有沒有那麼糟、自己有沒有那麼不快樂,會被當下的情緒漩渦不斷放大,而一旦在當下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總是否認自己會受情緒操控的人,事後就必須說服自己這麼做很合理,讓一個對關係有害、長久下來可能造成裂痕的相處方式變成習慣。
我在強調「人是非理性的」的行為經濟學裡,記下了這個重點並且加以警惕,在感到不快樂或負面情緒襲來的時候不要做決定, 否則到了事後,這個決定的影響還可能會持續下去。
有趣的是我發現另一半其實是無意識地選擇這個作法,雖然他也會有煩到當下臭臉,說些氣話讓我跟著生氣的時候,但更多時候他會選擇不說話,聽我把話說完就回房睡覺。雖然我就像大部分的女生那樣,覺得「吵架不是應該先和好再去睡覺嗎!」因為心情依舊煩悶而輾轉難眠,但隔天一早總是無法否認,在睡了一覺,消除了疲憊和忘卻了當下情緒之後,兩個人都覺得這不是一件值得吵成那樣的問題。
有些時候事情已經吵到一個狀態,尤其是那些假設性的問題, 是說什麼都無法在當下取得共識或者挽回和諧,這時候分頭去睡, 也未嘗不是讓彼此分開冷靜。
因為只讀了他一兩本著作,我對丹.艾瑞利的行為經濟學可能過度延伸,也不知道這樣應用在自己的婚姻哲學裡算不算切題,但對我自己確實很有幫助—永遠要記得,自己並不是自以為的那樣理性。
這種認識會讓我們對自己的判斷有所保留,在感到都是對方的錯而自己很合理的同時,也會自我提醒要去思考「事情或許不是那樣」,每個人都有自己覺得站得住腳的地方,在婚姻裡越是想要強調自己是對的,就越是可能全盤皆輸。
在感到不快樂或有所不滿,甚至因為身心狀況不佳,負面情緒擴大到覺得自己「不幸」 的時候,我會先克制自己不說。久了,發現這確實對我的婚姻也很有幫助。
(圖片來源:Pakutaso 16694)
(原文刊載於羽茜《在婚姻裡孤獨》/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