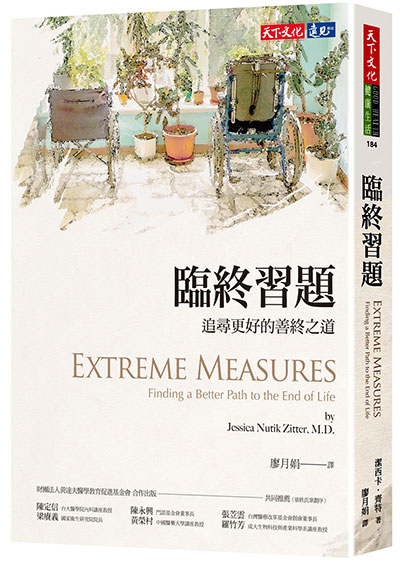幾年前,在一次家庭聚會上,我坐在泰瑞對面。她以前是緩和醫療社工,現已退休。我們就美國的臨終醫療照護,交換經驗。接著,她告訴我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年前,泰瑞一直在想死亡的事。雖然她身體還健朗,但親人都不在附近,因此擔心如果她生病,不能表達意見,可能會被醫療系統「挾持」,臨終備受折磨。有關瀕死前的過度醫療,她再熟悉不過。她已下定決心,萬一她沒有機會恢復健康,無法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她絕不想依賴機器活下去。她預立了醫療指示書,言明:
本人如有下列狀況,則不願以人工方式延長生命:(一)得了不治之症且病情將在短期內惡化、導致死亡;(二)失去意識,而且經過醫療評估將無法恢復意識;(三)治療的可能風險與負擔將超過預期效益。
接著,她告知所有親朋好友這個決定。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她預立了醫療指示書後不久,就因胸部劇痛被送到醫院。她最恐懼的莫過於這一刻。之前,她已在腦中演練過,也記得把預立醫療指示書帶到醫院。她把醫療指示書交給急診的心臟科醫師,明確告訴醫師:「我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醫師不可置信的看著她,以為她瘋了。醫師說:「你希望我們幫你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醫師解釋說,她得了心肌梗塞,最好利用心導管介入,做氣球擴張術或置入血管支架撐開冠狀動脈阻塞之處,並警告說,由於搶救心肌梗塞的黃金時間只有90分鐘。時間攸關性命,片刻延緩不得。
醫師說,但是心導管介入術並非萬無一失,如果她拒絕心肺復甦術,他就無法處置。因為導管可能戳破動脈壁,其他併發症包括引發危險的心律不整、心臟輸出的血液無法正常灌流到各個器官、中風、心肌梗塞等。再者,如果阻塞得太嚴重,無法利用氣球擴張,甚至當下會決定改成開心手術。由於隨時可能會有狀況,必須要給他應變的彈性,如果她拒絕心肺復甦術,就騎虎難下。
醫師說,時間一分一秒的溜走了。如她接受這種治療,復原的機率很大,風險很小,但是她必須明確表明意願。她願意嗎?
泰瑞堅持,她不願接上呼吸器,無論如何都不願這樣。她看過太多了,就她所見,結果都不如預期。「我願意接受導管介入術,但是萬一出了什麼差錯,就不要救我了,讓我走,可以嗎?」
醫師說,不行。「我不能讓你死在手術檯上,」他說,如果她不想接受導管治療,他可以請急診醫師開給她治療心肌梗塞的藥物,但效益遠不如導管介入。說完,他好像急著要離開了。
泰瑞攔住他,「那就做吧!」她說。於是她被十萬火急的推到導管室,因為從心肌梗塞的病人進入醫院、到施行氣球擴張術,必須在90分鐘之內完成。結果一切順利。泰瑞不必使用呼吸器,過了週末就可以出院了。儘管如此,她還是滿懷恐懼,因為在治療過程中,她可能變得沒有聲音,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沒有選擇的餘地。這個醫療體系讓她覺得很無助。
你要上船、還是下船?
許多專科醫師,如心臟科醫師和外科醫師,都會要求病人二擇一:「如果你不照我的方式,那就不要找我治療了。」這就像是開關。如果同意接受手術,那就不能拒絕心肺復甦術,也不能要求緩和醫療諮詢。反之,如果病人決定不接受心肺復甦術,就像前面提到的Z太太,就不能接受較積極的治療,儘管能緩和症狀或是延長生命也不行。
如果出了差錯,不如預期呢?儘管醫師已經盡力,她還是被送到加護病房,靠機器生存,那該怎麼辦?這不是她極力避免的噩夢嗎?她預立的醫療指示書何時能生效,以撤除維生系統?這種事真的發生過嗎?
泰瑞既已預立醫療指示書,你可能想知道:為什麼泰瑞的心臟科醫師不願照她的心願去做?我不知道這位醫師的動機,但我想,這可能和「30日死亡率」的手術統計數字有關。醫療體系會統計每一位醫師的病人術後30日內死亡的比率,藉以評估醫師的能力。
聯邦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和各州的衛生署都會參照這個比率來支付醫療費用,讓民眾了解:某一醫師或某家醫院的表現,是否低於該州或全美國的平均值。
理論上來說,病人在考慮接受手術時,會選擇病人死亡率最低的醫師或醫院。問題是,這種統計數字不但會衝擊到醫師生涯及其服務部門的聲譽,也會阻礙醫師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有報導曾指出,由於外科醫師擔心「30日死亡率」會變高,直到術後第31日,才願意讓病人接受緩和醫療諮詢;在此之前,則會想盡方法讓病人存活。我們不禁要問:醫師在做治療決定時,主要是考量到自己的名聲,還是病人的需求?
(圖/Shutterstock Gorodenkoff)
(本文作者為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專科研究醫師。原文刊載於潔西卡.齊特 Jessica Nutik Zitter M.D.《臨終習題:追尋更好的善終之道》/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