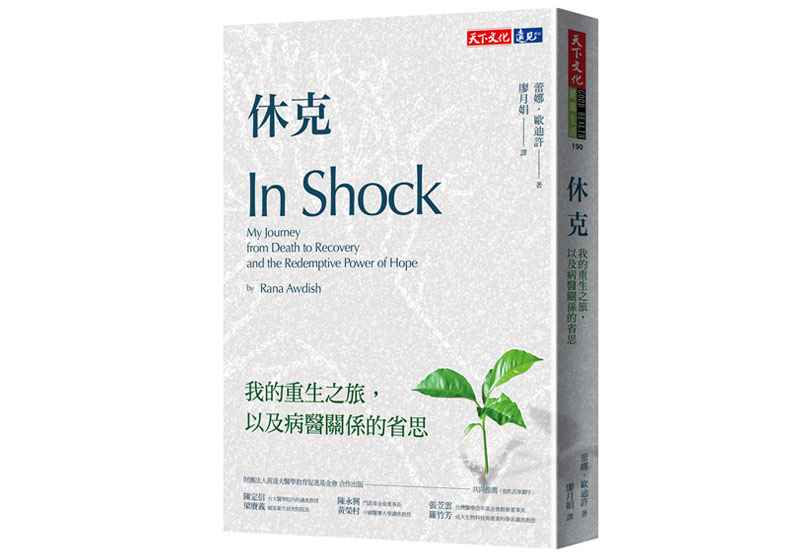當我們在治療過程中遇到無法救回的病人,醫學教育並沒有教我們辨識自己心理的創傷。搶救病人之後,我們不會跟團隊成員討論,甚至可能不再想這件事。同事照顧的病人死亡,我們頂多會在病例討論會上追根究柢,不會去評估同事的心理和情緒是不是受到影響。在我們的醫學訓練過程中,我們習慣讓同事獨自面對,不去干擾。我們完全不知如何處理恥辱的感覺,不知去哪裡告解。
身為醫師,我們老早就學習隱藏自己的情緒,也不會被別人的情緒拖下水。
現代醫學之父奧斯勒(William Osler)因為用心聆聽病人的聲音,而備受尊重,他在教育醫師時,特別提倡「平靜的心」(Aequanimitas),認為這就是醫師最重要的特質:「不管遭遇什麼樣的情況,必須沉得住氣、頭腦清晰,在風暴中冷靜自持,臨危不亂。」同樣的,在病例討論會上,同事討論你的疏失,你也必須處之泰然,和自己的情緒保持距離,不讓他人的情緒影響自己。
「平靜的心」要傳達的訊息是:為了做出明確的判斷,必須保持距離和冷靜。老師告訴我們,要成為一位好醫師,必須含蓄、內斂。我們都立志要成為好醫師,因此我們都接受這樣的教導,把這點當作是我們這一行的祕密。老師希望我們能在病房裡,表現得超然而獨立。
我在當醫學生時,曾與同學一起面對一位病童的死亡。先前我們看著醫療團隊竭盡全力救他,但他還是走了。我們應當離開病房,然後讓他的父母進來看他,但是我們被悲傷凍結了。主治醫師通知家屬之後,走進病房,嚴厲責備我們:「你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你們這種行為實在不成熟、實在輕率。如果你們懂一點醫學,就該知道死亡是無法避免的……要是你們為了這個孩子的死,陷入悲傷,就太不負責了。若像你們這樣,是要如何照顧其他孩子?」
我努力了解主治醫師說的,我因為過於悲傷,乃致忽略其他病人的需要,這樣的情緒反應不但幫不上忙,反倒可能害死其他病人。於是,我們很快學會封閉情緒。任何情緒只要讓別人看出來,就會招來這樣的評語:「也許你無法承受這麼多。你可能不適合做這樣的工作。」如果要哭,那就躲在櫃子裡哭,或是開車回家的時候哭,總之不能讓人看見你的淚水。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解脫束縛的辦法;但有的同學發覺情緒過於難纏,難以應付,於是沉溺於酒精等癮頭;有人離開行醫這條路,換另一個行業;有些人則自殺。
醫學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
我在紐約一家醫院內科擔任總住院醫師、輪調到感染科時,我帶的一位住院醫師表現不好。他常焦慮,曾犯了幾個錯,因此考核分數不佳。他被我們科的主管盯上了。主管會特別注意他開立的每一張醫囑和他的報告,看是否有不適任的證據。他因此焦躁不安,魂不守舍。有位病人抽血檢驗的結果是陽性的,他疏忽了,沒安排更進一步的處置。他開立的幾張醫囑有問題,有幾個檢驗數值的解讀也出錯。儘管如此,每一項疏失都有人及時發現、及時補救,病人都沒受到傷害。
雖然這些疏失沒什麼了不起,但主管不肯輕易放過他。由於我是總住院醫師,我每天都得監視他,看他做得如何。我報告說,他的情況更糟了,他開始自言自語。主管要求他到精神科接受正式評估。我們共事的那個月結束時,科裡幾乎所有的主治醫師都不讓他升級。他很可能必須重做一年,才能過關。
他在星期五得知科裡的決定,接下來就是7月4日美國國慶日的連續假期。星期五那天傍晚,他在五點鐘、六點鐘、七點鐘都打了電話給我。我覺得很煩,加上內疚,因此不想理他。他無法接受科裡的決定,在星期天自殺了。星期二,他沒回來上班,我們找不到人,才發現這個悲劇。
我對朋友說:「他是被我們害死的。」朋友表示恐怖或憐憫。他們搖搖頭,說這不是我的責任。但我百分之百認為這是我們造成的。「我們用懷疑和評斷害死他。他在嚴格的檢驗底下崩潰了,換成我們,一樣會受不了。」
科裡的主治醫師為我們打預防針,訓示我們:「聽著,顯然他不適合行醫。有些人就是不適合。」不斷有人提及他能力不足和自慚形穢;還有人說,韌性就像一種非黑即白的性狀,有人天生具備韌性,有人就是沒有。似乎韌性不需要經由對話、坦誠相待和同理心的文化來培養。其實,這樣的文化才有助於自我療癒,讓我們提供更好的照顧給病人。
說來,醫學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我們可以預期,每一個轉角都可能出現錯誤。由於醫學體系的錯綜複雜,失敗是無可避免的。就人體的設計來看,敗壞更是必然的。衰老已嵌入我們的遺傳密碼之中。病人會死,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把韌性內建到我們的體系裡?為何把悲傷視為意外的偏差?培養韌性的文化,有助於我們迎接各種經驗,也能幫助醫學社群所有的成員繼續生存下去。
第二位住院醫師從公寓窗口一躍而下,跌落到下面樓層的鷹架上。同學衝下去,想要救他,但他已沒有脈搏,四肢多處開放性骨折。我們的腦袋出現回音,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被悲傷淹沒,就不能照顧其他病人。我們的訓練就是教我們如何對死亡麻木—即使是自己的死亡、同事的死亡。
對醫學的局外人而言,這樣的故事太悲慘,沉重得讓人受不了,而我們又無法在自己的圈子找到一個安全的所在。我曾試著在腦袋下載一天的點點滴滴,希望從中找到安慰,但我總是陷入令人悲劇的細節。如果我想找個人傾吐,聽我述說的每一個人都只是把焦點放在事件上,不知我的情緒和需求。我變得易怒,覺得他們都沒聽出重點。我覺得更加孤獨了。
因此,我開始畫畫。我發覺,我可把不安和噩夢轉移到畫布上,從中得到慰藉。我利用象徵和顏料,把痛苦藏在色彩底下。我終於感受到久違的平靜。我手拿畫筆,讓印象浮現時,衝突的情緒就可宣洩出來。
藝術知道死亡。藝術了解這世間就是會出現讓人無法承受的悲劇。藝術像一面鏡子,可以把我們的感覺反射出來。是的,這樣的悲劇以前也發生過,但當事人還是撐過來了。或者他們沒能存活下來,但藝術還在。藝術代表他們所受的苦,透過藝術,我們就能了解他們。藝術提醒我們,我們的不幸一點都不新奇,痛苦與救贖的歷史源遠流長,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藝術很微妙。最初畫出來的東西總是單調而拙劣。一層又一層的顏料加上去,有了層次和深度,主題就呼之欲出。因此,最初的草圖只是建立基礎,之後再一層層塗上去,就能顯現出對比和先前忽略的地方。只有不斷審視,才能得到真正的了悟。
我畫了戴面具的女孩,她們安穩坐在船上、或是下半身在沉重、不透明的藍色水中。我畫的男孩穿軍服,戴著動物標本做的面具。他們傻傻的上了戰場,不知戰爭是死亡的威脅,也不知危險常偽裝起來。我畫一隻有星星標記的綿羊,離開一座小小的森林,來到一片空地,不知自己即將進入一座更大更黑的森林。我畫最寒冷的冬天。我畫一個髮色如紅銅的女孩,一臉愁容,坐著等待一個永遠不會來的人。我也畫繁花在鳥籠般的肋骨之間,恣意盛放。
(本文作者為美國亨利福特醫療體系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原文刊載於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休克:我的重生之旅,以及病醫關係的省思》/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