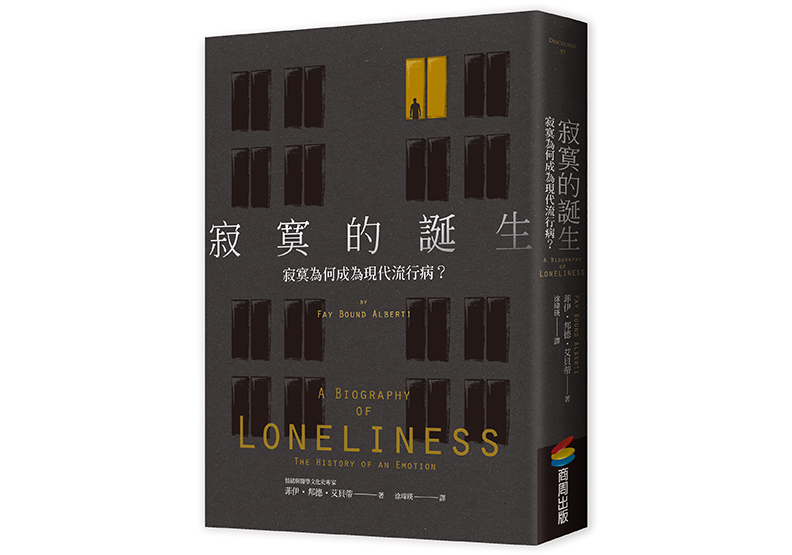所有階層的寂寞感都會受到科技創新的影響,而且「遠距離親密」(該詞用於描述數百萬名老年人的狀況,他們住在離家人有段距離的地方,但能透過視訊電話或訊息傳遞來交流)不一定會比近距離生活更糟,因為後者可能產生各種煩人的瑣事。不過,有個問題是:老年人對社群媒體的態度是如何形成的。
法蘭.惠特克—伍德(Fran Whittaker-Wood)在《哈芬登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銀髮網族的崛起:科技如何豐富老年人口的生活〉(The Rise of the Silver Surfer:How Technology Is Enriching the Lives of the Ageing Population),她在文中寫道:
❝人們假設老年人無法從數位科技中獲益,尤其是那些跟建立新社交網路以取代正在凋零的社交網路有關的科技,但這是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想法。❞
惠特克—伍德反對「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觀念,她認為老年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在網路上活動。她引用了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研究結果,指出超過65歲的成人有75%都會使用網路,且超過75歲的女性在所有人口群體中的增長幅度均為最大。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即
❝科技能夠顯著改善晚年的生活品質,長者也終於開始覺醒,意識到科技如何改變老化的面貌。 ❞
對於老年寂寞一直以來被視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該文過分簡化的措辭十分具有啟發性。是的,數位科技能為老年人的生活形態提供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法,包括與親朋好友的連結、社交團體,以及對醫療保健和科技等一系列商品及服務的取得能力。不過,老年人的寂寞和數位科技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相關性而已。就跟年輕人的寂寞一樣,數位科技並沒有為老年寂寞提供快速見效的解決之道,它們也不是解決「現實生活中」缺乏實質連結的方法。數位科技無法解決具身化的寂寞感,或是對實體接觸的渴望,反而是飼養寵物或許能解決這些問題。數位科技也不一定能緩解伴隨著哀慟及喪偶的脫節感,或是與同儕之間的孤立感。有些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是將自我的特定版本呈現給他人——通常是「快樂」、修飾過的自我,擁有緊密的家庭連結、經濟安全、朋友及和諧的家——這甚至可能導致負面比較和自尊心低落,進而增加孤立感和寂寞感。
社群媒體和數位科技並不會轉變社交關係
而是重現社交關係;人們在社群媒體上的互動往往與現有的連結形式並存,重現既有的互動模式跟習慣。在社交上感到脫節的寂寞老人,並不會因為使用臉書就覺得自己更加融入現實生活。
為了正面影響醫療與社會介入措施、支持政府降低社會所有階層寂寞感的目標、確保老年人不會被遺忘,我們必須根據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環境、經歷和期待,以實證、具有歷史根據的方式瞭解寂寞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這比英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比較性評估更加複雜,不過此舉將有助於瞭解國家與文化影響所帶來的衝擊。我們需要更清晰地瞭解老年寂寞的架構,對於青少年、單親家長、窮人、無家可歸者和任何已確立的弱勢族群也應該如此。我們在仔細關注這個領域時,也需要考量詞彙在一個社會中的不同時間地點,可能具有不同的含義;比如「老年人」和「社群」,又比如「寂寞」、「歸屬」和「家」。
(本文作者為情緒歷史學家;原文刊載於菲伊・邦德・艾貝蒂《寂寞的誕生:寂寞為何成為現代流行病?》/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