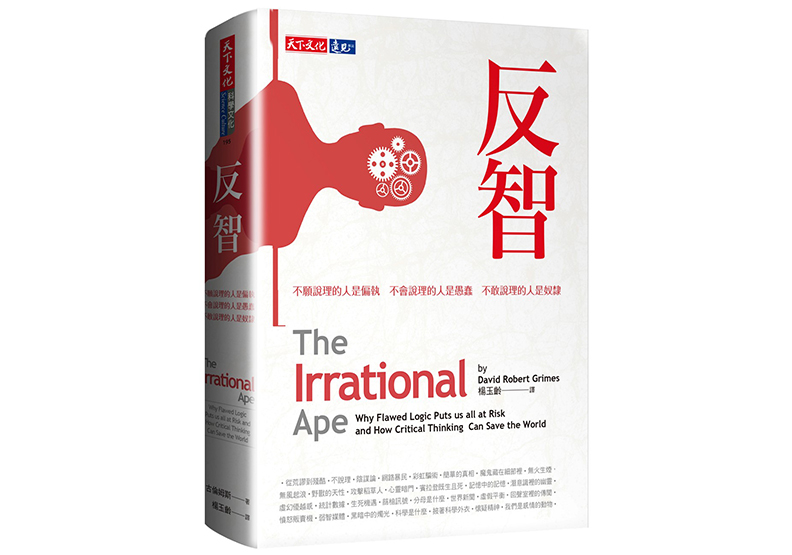編按:有一群熱心的疫苗反對者,把這則故事推進到主流媒體,來傳播給較容易受騙的記者。非專業記者以憂慮的發言者自居,強調自閉症特徵就在疫苗接種後顯現出來,鞏固了因與果的印象。(本文摘自《反智》一書,作者為古倫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以下為摘文。)
疫苗接種讓「天花」絕跡
二十世紀初,對免疫學的新見解,讓疫苗接種得以興起,全力對抗自有記憶以來便禍害著人類的疾病。天花是這張恐怖名單上的頭牌,到了1959年,它每年至少害死200萬人。
那一年,全球開始認真通力合作,用疫苗接種來對抗天花。到了1979年,天花病毒已經完全被消滅了。這是人類史上頭一遭,把一種致命病毒貶謫到史書和悲慘記憶中,只留下一點點,存放在世界各地小心控制的生物防護實驗室裡。
但是從很多方面看,疫苗卻淪為自身成就的受害者。天花這類疾病非常強悍,曾經是人類必須直面、無可逃避的,後來卻開始慢慢從文化自覺中淡出。人們不再會碰見滿臉痘疤的天花病人,也不會碰到因脊髓灰質炎而跛足的人。曾經縈繞人心的,導致孩童喪命或耳聾或腦殘的麻疹傳染,也不再是一般人共通的經驗。
隨著這方面的風險愈來愈抽象和不顯著,自滿開始滲入人心。人們忘了接種疫苗曾經多麼深刻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在二十世紀末,年輕的父母不像當年自己的父母;年輕的父母已不用擔心孩子會在嬰兒期死亡。嬰兒能活下來,如今已成為肯定的事,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有些年輕的父母發現了一些新的恐懼,很令他們憂心。
沒有證據支持的記者會與擔憂一拍即合
其中一項愈來愈大的憂慮是關於發展障礙。二十世紀晚期,自閉症在兒童中的發生率明顯開始升高,嚇壞了為人父母者。泛自閉症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特徵,往往就在幼兒剛接種疫苗後不久顯現出來。在有些人看來,這便暗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意涵:會不會是接種疫苗本身引發了自閉症?
然而,沒有醫學證據支持這樣可怕的結果,倒是有很多與此矛盾的證據。原本這個偽造的關聯可能會從公眾意識的周邊漸漸消退,要不是惡名昭彰的英國腸胃科醫師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搞出了那些動作。
1998年,韋克菲爾德和12位同儕,聯合做了一項很小型的研究,對象是12名自閉症兒童。研究結果發表在醫學期刊《刺胳針》上,宣稱發現了一群伴隨自閉症而產生的腸道症狀,他們將它取名為自閉症型腸炎,而且在該篇論文的討論部分,深埋了一個相當揣測性的暗示,認為這有可能與接種麻疹疫苗有關。這個暗示就像是一個很隨意的嘗試性的主張,毫無確證的資訊。
正常情況下,這樣淺薄的臆測一定會被駁斥為沒有根據,但是韋克菲爾德不受嚴謹科學行為的束縛,他使出了很不尋常的一招:直接召開記者會!韋克菲爾德宣布,他發現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三聯疫苗)與自閉症有關聯,因此這種三聯疫苗不安全。此一宣稱,剛好與自閉症日益普遍所引發的擔憂,一拍即合。
至少剛開始,韋克菲爾德的驚悚宣言對公眾論述沒有產生太大效果。他的說法與許多更強大的數據相悖。科學記者和健康記者都夠精明,能看出含糊可疑的科學說法的特徵,也會提防韋克菲爾德過度的自吹自擂。
媒體成了「大眾恐慌」的推銷者
然而漸漸的,有一群熱心的疫苗反對者,把這則故事推進到主流媒體,為了規避科學新聞的守門員,便把它包裝成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來傳播給較容易受騙的記者。非專業記者以憂慮的發言者自居,強調自閉症特徵就在疫苗接種後顯現出來,鞏固了因與果的印象。對於反疫苗運動人士來說,他們本來就需要大眾恐慌,以便推銷自己的想法,這無疑是天賜良機。
雖然對MMR疫苗疑神疑鬼的高峰,在2000年代初也許就已平息,但是那個年代的兒童受害者卻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對疫苗接種有疑慮的父母,拒絕讓子女受到防護,而他們的恐懼又漸漸擴散到全世界。

那些成長期間沒有接種疫苗、或是缺乏群體免疫背景的幼兒,在美國的結局是可以意料到的。曾經完全擺脫麻疹的美國,如今也看到感染率在某些地區升高了。
2014年,在27個州共有677宗病例,達到20年來的高點。隔年,單獨一名感染者在迪士尼樂園造成至少150個病例,有關當局還注意到「2015年的麻疹爆發可能要歸咎於疫苗接種率低於標準」。2019年初,紐約也出現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這些人都是疫苗恐慌史的遺禍的受害者,而反疫苗運動人士到現在仍致力推銷這份恐懼。
全球十大健康威脅:「疫苗猶豫」
這個問題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次將「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列入全球十大健康威脅。支撐MMR疫苗恐慌的,只不過是觀察到自閉症的顯現是在疫苗接種後不久。
這個巧合的時間點被當成了特洛伊木馬,讓狂熱的反疫苗人士把「後此謬誤」推銷給天真的人,煽動了整起毀滅性的風潮。至今我們仍能感受到的不幸後果,正是一個顯著的提醒者,提醒我們錯誤思考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這份恐慌裡,還有另一個因素在煽動:當代的文化思潮和時代精神。回頭看這整件事,我們可能會好奇,為何有這麼多的擔憂被耗費在假設的自閉症風險上,以及為何與人們更為一致的是那份恐懼,而不是疫苗接種能預防什麼。
部分答案在於「可得性」。對於2000年代初期的父母來說,孩子因麻疹而死亡或永久傷殘的影像及故事,壓根兒就不在我們的文化詞彙中。由於許多年前的研究以及公衛上的努力,麻疹病毒禍害的鮮活畫面不再頻繁出現,因此也和憂心的父母缺乏共鳴。
「疫苗恐懼」成功的原因:感知偏差
反觀自閉症,在現代經常有人討論,是公眾語言的一部分。雜誌和報紙時常刊載自閉兒童面臨挑戰的故事,以及揣測自閉症比率明顯提升的背後成因。從前這些長期住在收容機構、缺乏自理能力的孩子,對社會來說幾乎是隱形的,但是現在卻突然出現在大眾眼前了。
「自閉症」這個想法很容易進入大眾心中,麻疹的毀滅性衝擊如今卻不能。而這種概念上的可得性差異,會讓我們的感知產生很大的偏差,而且是悲劇性的偏差。
這種「更看重容易取得的資訊、或是最近的資訊」的現象,叫做「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s)。在評估一個概念或是形成一個意見時,這其實就是一條心理捷徑,依靠容易想起來的最接近的案例。它依據的假設是:
❝如果某樣事物很容易想起來,那麼這樣事物必定很重要;或者說,它至少比其他替代的解釋更為重要。愈容易想起來的資訊,我們對它愈有信心。❞
事實上,這通常會讓我們的意見偏向最近的消息或是記得住的案例。但是,某個消息是最近的或能記得的,並不代表它就是真實的,根據這種捷思途徑得出的結論,也不能算是嚴謹的。憂心忡忡的父母更容易接觸到可怕的自閉症故事,而非麻疹死亡案例,即便麻疹的危險遠超過並不存在的自閉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