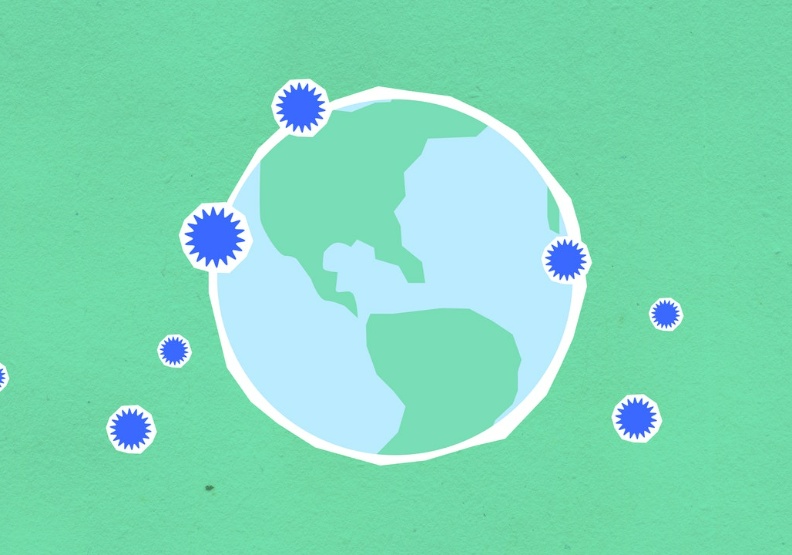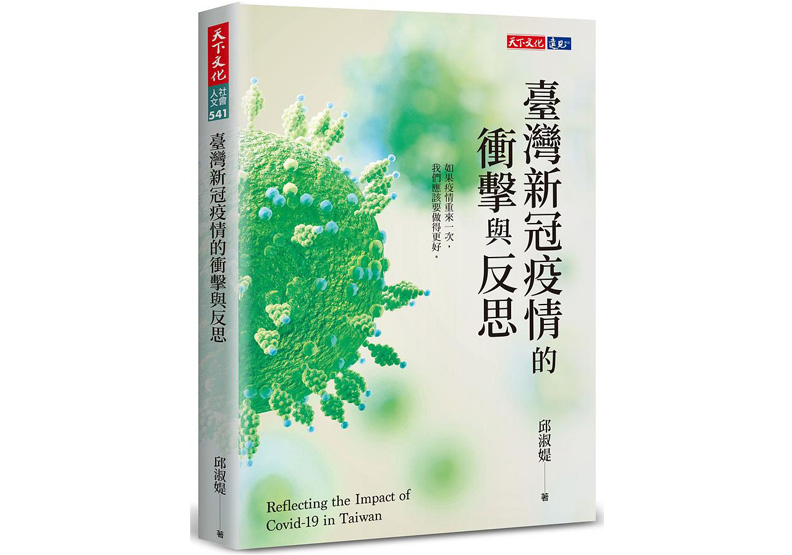新冠疫情攻進全球已達兩年半。在高度全球化、科技化與資訊發達的21世紀,人類共同體驗了始料未及的衝擊,而且,隨時間過去,大家發現,後患無窮,影響深遠,不是疫情結束就沒事;整個殘局很難收拾。
如果時間倒轉,一場災難能否避免?
既然如此,大家忍不住要問:這樣的瘟疫與重大衝擊,真的完全無可避免嗎?
到底,世界衛生組織(WHO),乃至各國政府,在最關鍵的時刻,錯失了什麼、為什麼會錯,以至於有這樣的疫情發展?
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能做對了什麼,整個結果,是否可能完全改觀?
做該做的事,在一開始或許看起來很難下決定,但,不下決定的話,不僅以後代價更高,而且有可能就回不去了!在看WHO宣布哪些事項、各國做了多少努力的時候,很重要的是,要不斷檢視:缺了什麼(而非有什麼),才不會眼花撩亂。做對,比做很多,更重要!而在防疫路線的抉擇上,事實也證明,成效最好的事,成本反而是最低的。
試想,如果WHO在1月30日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是建議各國同步啟動旅遊管制、暫時性鎖國,並進行境內潛藏病例的清零工作,疫情嚴重者搭配較強之公共衛生措施(例如停課、停班、暫停大活動等)降溫,然後,在認證過後,啟動清零成功國家之間的商旅泡泡,鼓勵其他國家跟進,終至全部解封⋯⋯,會不會,在3-4個月或半年左右的時間,疫情可能獲得控制,也不至於衍生愈來愈難纏的變異株?
全球往來密切,傳染病交互影響,若無法有全球共同的防疫決策與步調,麻煩就沒完沒了。
第一次要做這樣的決定,或許很難。但,經一事、長一智,如今知道了:若不忍半年,可能就需要忍兩、三年或更久,而且要多付出數億人感染、超過一千萬人死亡、大量長新冠與數不清的經濟代價,人們總要想想,未來能否更早發現、做出更明智的決定?

WHO在關鍵時刻做了什麼、少做了什麼?
據WHO之大事紀,WHO中國辦公室於2019年12月31日向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簡稱IHR)西太平洋區署駐點通報,WHO旋即陸續進行一系列措施,包括通報會員國、啟動疫情新聞報告、發布中國方面已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也提出了一系列指引供各國使用,包括:感染預防與控制、檢驗、國家應變量能檢視工具、風險溝通與社區參與、防疫設施與物資清單、臨床指引、病例監測定義、旅遊建議等。WHO在2020年1月11日獲得中國大陸所提供的病毒基因定序。WHO歐洲區署1月24日接獲法國通報歐洲第一例境外移入病例,次日發布聲明指出地方與國家層級應做好病例發現、檢驗與臨床處置的準備。
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宣布將此新型傳染病列為法定甲類傳染病,於1月23日對武漢實施大規模公共衛生措施,包括封城(陸、空交通之封鎖/管制)、擴大檢驗、醫療資源緊急擴充與調度、確診病人集中治療、強制戴口罩、強化封城期間之社區公共服務措施等;隨著疫情擴散,封城措施亦迅速擴大至湖北省與多個城市、地區,積極阻斷,再隨疫情改善而放寬,最終在各城市/地區陸續達到清零而完全解封;湖北省及武漢市先後於3月25日、4月8日解封。
WHO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於1月27、28日率高階代表團抵北京拜訪習近平以了解中國之防疫措施,並於1月30日第二次國際衛生條例緊急會議後,召開記者會,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簡稱PHEIC),為2009年以來,第六次宣布PHEIC。當時全球在中國以外僅有98個病例、尚無人死亡。
WHO提出七項建議,第一項為:「沒有理由採取不必要之國際旅遊與貿易干預措施;WHO不建議限制貿易與移動」;其餘六項為:WHO將協助醫療體系較弱的國家;將加速疫苗、治療與檢驗等藥物發展;打擊謠言與錯誤資訊;檢視與強化物資整備;分享數據、知識與經驗;以及國際合作。記者會上,多位記者質疑:若不限制旅遊,宣布PHEIC有何意義?譚德塞與其首席專家Mike Ryan表示:此一宣布的重點是考量「病毒可能衝擊醫療體系較弱的國家,需要加強整備」,但反對沒有科學證據的不必要做法;旅遊或貿易限制是沒有必要的。
在2月11日,此新型冠狀病毒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二代」(二代SARS病毒,英文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標準縮寫為SARSCoV-2),其引發之疾病定名COVID-19(一般譯為新冠肺炎),而其病毒亦稱為新冠病毒(COVID-19 virus)。
隨著疫情傳播至各洲,世界衛生組織於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為一個全球大流行(pandemic),當日新病例數為7,659例。各國採取不同防疫路線之樣貌已然浮現,但譚德塞表示:伊朗、義大利、南韓正採取行動以遏止擴散,但正如中國,這些措施正對社會與經濟造成沉重代價,所有國家應在保護健康、使經濟與社會失序最小化以及尊重人權之間求得平衡。此談話透露一個全球衛生關鍵領導者面對全球大流行之態度,是認為健康、經濟與社會秩序相互衝突、必須取捨,暗示不可為健康犧牲其他二者,這種態度影響其對全球防疫方向之領導。他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但或許是唯一最不該這樣想的人,因為其後各家之研究分析,證實事實恰恰相反,而全球原本仰望他能對各國做出正確帶領。

此後,隨疫情擴散,病例數呈指數型成長,加上Alpha、Delta、Omicron等傳播力愈來愈強的變異株出現,發生率迭創新高,2021年1月初單日新增約90萬例、2021年底以每日百萬例計。每日死亡人數亦隨發生率上升,2021年1月底達最高峰,單周約10萬人死亡;隨著疫苗推廣,雖重症率降低,但感染人數居高不下,2021年死亡人數大致都比尚未施打疫苗的2020年同期還高,在Omicron席捲之後亦衝到每周7萬人以上。顯示欲減少傷亡,恐不能只靠疫苗。
迄2022年1月1日止, 全球超過2億8千萬人染疫、超過541萬人死亡。「全球大流行整備與應變獨立調查委員會」(WHO依2020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所成立,以下簡稱「獨立調查委員會」)綜整,除了生命損失、醫療體系衝擊,新冠疫情造成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全球經濟損失是二次大戰以來最深,疫情最嚴重時曾達90%學童無法上學,性別暴力求助需求成長五倍,一億多人被推入極端貧窮,全球永續發展多項目標進度亦隨之延宕。
防疫決策三大迷思
在全球疫情初發的30天,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反應可謂迅速,包括立即訂出防疫指引、宣布國際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並在病例數指數成長之初即宣布為全球大流行;WHO祕書長每日召開記者會,持續了兩年。然而,疫情為什麼仍一路失控?顯見不是沒有努力,而是需要檢討其決策思維與戰略選擇上出了什麼問題。
許多西方國家與WHO有類似的思維,並同樣採擇了所謂的佛系防疫路線。國際上已有許多研究分析佛系與魔系路線在防疫結局上的迥異,皆獲得一樣的結論。而臺灣在SARS時是否曾有類似思維?此次是否有類似錯誤?皆值得加以對照,作為未來面對新興傳染病之借鏡。
檢視譚德塞與各國防疫對話,可看出三大常見迷思:
1.以醫療模式進行新冠防疫:
傳染病防治對策,需考慮疾病嚴重度與衝擊(是否會造成大量傷亡與後遺症)、疾病表現(是否容易從臨床區辨)、傳播特性,與醫療在預防上與治療上之效果。很不幸的,新冠肺炎初期,在這四點上面,都不適合採取醫療為主的防疫模式。
新冠肺炎之嚴重性,初期估計致死率在1%~2%或更高,雖比SARS(約20-30%)低很多,但比一般的季節性流感高十倍以上,加上其傳播力強、能在短期內感染許多人,衝擊性不可忽視。然WHO與許多西方國家在初期對此有所誤判。對一個不確定威脅,未採取謹慎為先的風險管控策略。
新冠之疾病表現是善於隱藏,無症狀或症狀類似一般疾病,使病人未必就醫、就醫亦容易誤診。在傳播上,新冠肺炎具無症狀傳播之特性,且在潛伏期就能傳播,凸顯善用檢驗,使病毒現形之重要。最棘手的是除能飛沫與接觸傳播,亦可經由空氣傳播,易造成超級傳播事件,需搭配對於大眾的非藥物介入(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加以控制,無法由醫療體系執行。
在治療上,疫情之初並無能大幅提升存活率的特效藥。其後發展出單株抗體與抗病毒藥物,價格昂貴、難以普及,且須在發病初期及早用藥,高度仰賴檢驗資源,且在無症狀即能傳播之特性下,若與病毒共存,恐須將檢驗納入日常活動來執行。在預防上,雖快速發展出疫苗,然取得與分配不均,且疫苗雖有效減少重症,卻難防傳播。未以公共衛生手段阻斷,導致新型變異株不斷出現,威脅到疫苗保護力,亦使得不論透過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種,想達成群體免疫之希望皆落空(註:群體免疫是指在一部分人因感染或疫苗而產生免疫力之後,靠他們阻擋傳播,能將有效再生數(Rt值)降至1以下,使該病難以大量流行,而保護到還沒有免疫力的人)。
事實上,醫療體系本身在疫情下特別脆弱,成為直接(受感染)與間接(醫療崩潰)的「受害者」。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醫護死亡人數超過17,000人。醫療崩潰排擠正常醫療照護之提供,或病人因擔心感染而不敢就醫,也導致各種急重症之處置、手術與慢性病醫療等遭到排擠。疫情下的醫療體系,猶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2.忽略法律與治理,置責任於個人:
除了誤以為各國對抗病毒最重要的是醫療,WHO也忽略法律在傳染病防治之重要性,未嚴肅指引各國政府如何透過立法與執法,使科學上證實有效的保護措施得以普及性落實,以保護最沒有能力趨吉避凶之弱勢者。相反的,將責任委嫁於個人,試圖透過宣傳達到民眾行為上的配合,並認為如此即可減少傳播。
例如宣布Omicron為高關注變異株時,要求各國共同上傳基因定序、監測疫情之外,就是提醒個人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打疫苗等。然而,維護大眾安全的事項,涉及干預個人行動或行為自由、侵犯隱私等,必須有法律基礎,作為政府行使公權力之依據,避免政府在防疫上之過與不及,包括濫用權限以及怠惰不作為;此外,透過公權力亦較能確保各項措施能普及而一致的落實,避免因個人配合之落差,產生防疫破口(例如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而且,良好疫情管控較能避免惡化健康不平等,例如,高社經階層者在資訊、上班地點與交通方式之自主度上較高,但社會底層者則可能從事較高風險之實體勞動或服務、需搭乘大眾運輸等;透過公權力達到良好控制,則各階層都一樣安全,而若疫情嚴重,透過上班類型之管制或安全要求,亦可減少弱勢者承擔之風險。
國際衛生界早已提倡透過政策與治理,來達到更好的健康保護與健康促進,例如1986年WHO發表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即強調建立有利健康之公共政策(包含法令),而2016年發表之上海宣言,亦強調全政府、全社會、跨部門合作的健康治理,2021年發表之日內瓦福祉憲章,強調疫情暴露出生態、政治、商業、社會等決定因子對健康與健康不平等之衝擊,呼籲應根本導正價值觀與行動,重視福祉導向的經濟與決策,以促進永續發展多贏目標之實現。WHO忽略上游決定因子,未倡議各國政治領袖強化政府治理,反而消極地將責任轉嫁於風雨飄搖下無助的個人,暴露其專業素養之不足。
3.健康與經濟究係「魚與熊掌」或「唇齒相依」:
決策者在選擇防疫模式時,最常談到的難處,是該不該為健康而犧牲經濟與人民自由,認為非到最糟情況,不應輕率採用高強度措施。於是,總是錯失防疫先機,弄到情況難以收拾,而經濟是不是有保住呢?
經歷一場全球性的實驗,關於防疫究竟是在犧牲經濟或救經濟,是互為拮抗、或唇齒相依,相關實證在疫情第一年就已浮現。Our World in Data於2020年登出一分析,比較38國在2020第二季經濟表現與防疫表現,發現兩者呈正相關:防疫表現佳(新冠死亡率低)的國家,經濟受創愈輕微;而新冠死亡率愈高者,經濟受創愈嚴重。當時臺灣幾無死亡,經濟也幾乎完全不受衝擊,是當中受創最輕微者;而英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到了第二季仍受挫達21.7%、22.1%、17.3%,並賠上全球最高的新冠死亡率。其附註指出,未將中國納入比較,因其疫情發生較早,第一季經濟較前一年同期下挫6.8%,第二季則已成長3.2%。試想,若中國在發現疫情時,怕封城影響經濟而不積極介入,其死傷會如何、第一季第二季之經濟表現又會如何?
《刺胳針》醫學期刊於2021年4月登出在疫情一年後的分析,比較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採取不同路線(清零目標的魔系策略,或溫和減災的佛系策略)對其一年兩個月以來疫情期間新冠死亡率、經濟表現與封城強度之影響,發現:採取魔系策略的國家,不僅持續將死亡率維持在最低範圍,且經濟衝擊持續較佛系國家輕微,一進入2021已開始呈現經濟正成長。更重要的是,影響人民自由的封城強度,魔系國家僅在2020第一季較佛系國家高,清零後則大都時間維持在較低的封城強度,也就是人民大多享有比佛系國家更高的自由度。各國谷歌行動大數據(Google Mobility Data)亦顯示,每當疫情高升,不論政府是否宣稱與病毒共存、封不封城,民眾皆會自動限縮外出活動。
全球實驗揭曉,忌憚於傷害經濟與自由、不積極防疫,反傷經濟與自由更深更久。健康與經濟、自由之間是唇亡齒寒,而非魚與熊掌。可惜WHO與大多西方國家都以經濟為本位思考,認為公共衛生是在干預經濟與自由,根本未善加運用,導致全盤皆輸;輸了又宣稱有助於群體免疫,悲劇就一再重演。
WHO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新冠疫情之衝擊是否可避免、如何避免,進行調查分析。其報告指出,中國在1月23日武漢實施重大公共衛生介入之前,情勢嚴峻,絕大多數(86%)病例未被發現、基礎再生數(R0)可能高達5.7;到1月24日,已知無症狀感染存在之特性與疾病嚴重性;譚德塞在1月27、28日拜訪北京時,中國大陸已經採取封城、交通管制與一系列公共衛生措施,力求清零。然而,1月30日IHR緊急會議在宣布國際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卻沒有分享其做法及呼籲各國參考其經驗,且反對邊境管制,與當時已經存在的資訊與經驗背道而馳。而歐美各國的反應,亦同樣未借鏡其做法。最關鍵的失誤,就是疫情初期的處置失敗,包括WHO與各國,在防疫決策上錯失關鍵時機,且戰略錯誤。
(本文作者為前國民健康署署長,陽明醫學院醫學士,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碩士,臺灣大學流行病學博士;原文刊載於邱淑媞《臺灣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