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我工作表現如何,一旦開始照護家人,就只有離職這條路可走。」
這種為了照護而辭去工作的「照護離職」不斷發生,並在社會上掀起巨大波瀾。這不但害得企業失去人才,照護的日子一旦拉長,更會導致親子共同陷入貧窮與無助。換句話說,照護離職影響的不僅是現在,更會進一步對未來的人生造成阻礙。
其實照護離職的問題存在已久,但是,沒有實際照顧雙親、家人經驗等,就很難正視它的存在。那麼,為何現在這個問題會重新被人提起?
為了照護而離職,衍生的問題比你想得多更多
根據統計,全日本為了工作、照護兩頭燒的人,已超過240萬,其中大約有10萬人正面臨「是否要因照護而離職」的窘境。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換句話說,我們再也無法對「照護離職」這個議題視而不見。
照護離職的年齡層,大多落在40~60歲之間。這年齡的人一旦辭掉工作,便很難再次就業。照護離職後,不光是因為收入中斷而被壓得喘不過氣,在身體及精神上,更會被逼到走投無路,甚至出現虐待病患、照護者自殺或殺人等人倫悲劇(相信各位都曾在電視新聞上看過類似報導)。
再看企業方面,照護離職者大多正值壯年;尤其主任級以上的人,更占了全體近三成。在組織內擔任要職的人突然辭職,將導致業務流程陷入短暫的混亂,儘管最終還是得找人來填補缺額,卻無法避免離職當下造成的損失。
另外,這些年收入較高的職員一旦辭職,收入也就歸零,自然不需繳納所得稅,這對國家來說,即使只是一小部分,整體稅收仍會減少。
政府早就察覺此現象帶來的隱憂,為此,日本首相特別在第三次拜相的記者會上,發表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新三支箭策略。裡頭特別提到「零照護離職」的概念,可見其造成的社會問題已相當嚴重。
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突然面臨照護問題。若你還認為「我家兩老都還很年輕,所以不會有問題」、「我爸媽身體很健康,應該不至於突然倒下」,那就太落伍了。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按:類似臺灣的行政院社會司及勞動部)2016年1月提出的《照護保險事業狀況報告》,75歲以上的高齡者中,約有32.4%,也就是大約有529萬人,處於要人照護的狀態,今後這樣的人口還會不斷增加。(按:據內政部統計,2017年2月,臺灣老化指數首度破百,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首度超過幼年人口,平均約每5名青壯年,就要撫養一名老人;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更推估,全國78萬失能人口中,65歲以上老人就占七成六。)
相對於此,照護者(caregiver)的年齡層,則持續下修、日益年輕化,據說未滿30歲就扛起照護責任的「青年家庭照顧者」(young carer),少說有17萬~20萬人。因此,除非你出生至今都是孤家寡人(無父無母、也沒有任何需要照顧的人),否則任何人都可能面臨照護問題。
不僅沒了工作,更沒有自己的生活
我從32歲開始照顧失智的母親。我的母親罹患憂鬱症,不久後併發了阿茲海默症型失智症(Alzheimer's-type dementia),截至2017年5月,我已和她同住、照護了14年。我的母親沒辦法管理金錢、三餐無法自理、沒有時間概念,無法自行安排一天行程。她甚至曾經因為無法判讀藥包上的資訊,而不小心吃錯藥,相當危險,生活起居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我原本擔任房地產開發專員,人生卻在32歲時發生驟變。剛開始我一肩扛起所有的照護工作,終致陷入走投無路的狀態。我這才意識到,光靠我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戰勝眼前的難關。
就算我想蒐集與照護相關的資訊,也完全不知從何下手。我明明就那麼需要幫助,身邊卻沒人願意伸出援手,這種人情冷暖令我氣結,心中的焦慮更是揮之不去。現在看來說,當時的我一再退讓、不斷忍耐,終於把自己推進「眼前的一切都是敵人」的死胡同裡。那段期間,我的心彷彿一座長滿了荊棘的陰暗森林,個性變得頑固,完全失去了自我。我每天都在生氣,氣自己只能眼睜睜看著,原本應該全力衝刺的三十多歲人生,竟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

還記得剛開始照顧母親時,我經常向公司請假,久而久之,我開始反思:「也許我根本不喜歡這份工作。」於是,便有了「先暫時離開職場,之後再重新開始」的念頭,最後我真的向公司遞出了辭呈。
然而,我在離職後立刻發現:就算離職,照護該做的工作一樣也不會少,同樣漫長得令人絕望。接著,就是沒工作、沒收入、遭到社會遺棄,最後落得孤老終身的悲慘結局。之後,我偶然得知某個聚集了眾多照護者的團體。我原本就是個獨來獨往,就連上廁所也自己去的女孩,所以我很不喜歡那種一群人窩在一起發牢騷、抱怨、互舔傷口的場合。但我同時也想知道,其他照護者面對各種問題時,究竟是如何克服的? 所以我還是鼓起勇氣出席了某次聚會。
過去從來沒人願意聽我傾訴,這裡的人卻讓我暢所欲言。我邊說邊流淚,最後甚至放聲大哭,實在非常失態,但大家不斷鼓勵我、並肯定我的努力,展現了無比的溫柔和包容。同時,聽完其他人在照護上遭遇的種種苦悶後,我才發現「原來不光是我一個這麼辛苦」,這不禁讓我備感安心,並神奇的重新振作起精神。
在這之後,每當遇到與照護相關的煩惱或不懂之處,我只要開口詢問,前輩或團體裡的工作人員,馬上就能提供解答。這個團體簡直就像個照護資訊寶庫。也就是說,這些擁有照護經驗的人,正是每個照護新手的最佳導師。然而,很多照護者不知道自己的經驗這麼有價值。他們每天光是照顧親人就夠忙了,哪還有多餘的時間替自己發聲?但若忽略這些寶貴經驗,實在非常可惜。
此外,這些離職照護者的聚會大都選在平日,在地方上的公民會館舉行,在職者很難有機會出席,且聚會上談論的內容也不會刻意對外公開。「如果有那種可讓在職照護者參加,同時又能將資訊公開透明的聚會,不是更好嗎?」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在2013年發起每週六在市區咖啡店舉行的「在職照護者個人照護聚會」。
隔年,我主持了由WEB UNION株式會社(位於東京澀谷區)協辦的工作&照護協調研究所(Work & Care Balance Laboratory),持續推動以「你的經驗將成為某人的力量」、「No More 照護離職」為標語的照護者支援活動。之後,我更在2016年,成立一般社團法人照護離職防止對策促進機構(KAigorishoku Boushitaisaku Sokushinkikou,簡稱KABS),不論是由行政機關主導,或個人居家的照護,我們都積極介入了解,企圖降低因照護而離職的人數。
兼顧工作與孝道,你才能真正喘息
照護者最大的不幸是無從選擇,惶恐於眼前的局面、迷失人生方向,以為「開始照顧家人後,就非得辭掉工作不可」,但這樣的做法不見得正確。
你並非一定得辭去工作,才能妥善照顧生病的家人;儘管照護期間漫長難耐,你仍然可以像過去那樣,按照自由意志規畫、實踐人生目標。照護者一般都以親人為優先,但其實你得把自己的人生放在第一順位。總而言之,照護與工作(人生)可以兩全,無須自斷一臂。同時,我也深信,對於受照護的一方而言,唯有看見對方臉上帶著笑容,他們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照顧。
我在這本書裡,蒐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照護者心聲。他們分享了許多兼顧工作和照護的智慧與技巧。此外,我也整理了由政府及企業,陸續推動的各種長照制度和環境規畫,試圖阻止照護離職持續惡化。
我之所以公開這些資訊,無非是希望建立一個,能讓照護與工作兼顧且合理化的社會。實際上,我認為兼顧工作和照護,根本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本來就應該這麼做」。你不能只是被動的等待,而該主動爭取。因此,我會在書裡,透過各個照護者的故事,傳達照護不離職的具體方法與相關資訊,希望這些具體的實際案例,能讓大家有所啟發並採取行動。
前面談了這麼多,好像有點大放厥詞了,但老實說,多數的在職照護者(包含我在內),與其說是兩者兼顧,還不如說我們一直處於「咬緊牙關不離職」、死命硬撐的狀態。照護的確不是件輕鬆的差事,但這不僅是正視自己生涯規畫的契機,更可以透過照護,習得更多難以言諭的人生之道。
照護工作並非只有艱辛和苦楚,更是人生進階的新課題。假使各位讀完這本書,能更加同理、了解照護工作,並從中獲得堅持下去的勇氣,那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圖片僅為情境配圖)
(原文刊載於和氣美枝《照護爸媽,我得離職嗎?》一書/大是文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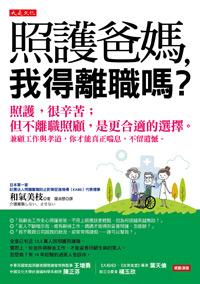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